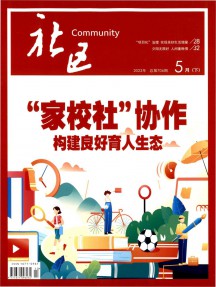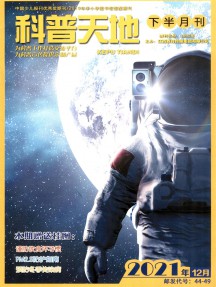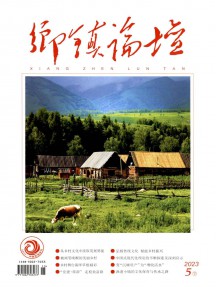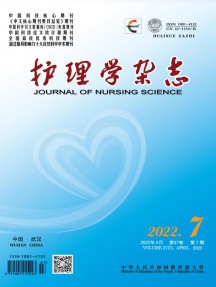社區(qū)治理的困境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間:2023-11-08 10:50:53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社區(qū)治理的困境,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07-0021-02
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開始了“村改居”的工作,它是城市化下一種新的社區(qū)模式,不同于城市社區(qū)居民治理的模式。
一、“村改居”社區(qū)的興起及其特點
“村改居”工作興起于21世紀(jì)初,是中國城鎮(zhèn)化過程中所特有的現(xiàn)象。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jīng)濟平均增長速度達(dá)到10%,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進(jìn)一步推進(jìn)了“村改居”的工作。在經(jīng)濟發(fā)達(dá)地區(qū),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在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上基本擺脫了傳統(tǒng)第一產(chǎn)業(yè)的束縛。再者,在城市建設(shè)的過程中,農(nóng)村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生活方式在城鎮(zhèn)化的進(jìn)程中發(fā)生著巨大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卷入城市化的洪流中,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統(tǒng)計,我國城鎮(zhèn)化率從2000年的32.6%增長到了2012年的52.6%。北京的城鎮(zhèn)化發(fā)展尤為迅速,城鎮(zhèn)化率增加近20個百分點,除北京與天津外,其他省份城鎮(zhèn)化發(fā)展也處于加速階段,從1995年到2008年,福建、江蘇、浙江三省城鎮(zhèn)人口比重均增加25個百分點以上[1]。城鎮(zhèn)化的迅猛發(fā)展,使得一些省市“村改居”工作發(fā)展迅速,如膠州灣海底隧道建設(shè)擠占土地導(dǎo)致4個村村民的集中安置,直接由農(nóng)村村落成為城市社區(qū)。濟南市到2004年底,“村改居”數(shù)量就已經(jīng)達(dá)到了102個,占城市社區(qū)居委會總數(shù)的25%[2]。
“村改居”的興起主要是經(jīng)濟發(fā)展與城市化的推動,這一城市化下的產(chǎn)物,有自身的特點。第一,社區(qū)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zhuǎn)變。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原來的村委會一夜之間掛起了社區(qū)居委會的牌子,但并不意味著成為城市居民委員會,它是邁入純城市社區(qū)建制的過渡階段。原來的村委會工作重心在經(jīng)濟上,村主任總把修道路,挖井種樹等事情的處理狀況放在工作的第一位,而把一些公共事務(wù)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現(xiàn)在“村改居”的社區(qū)居委會,逐漸進(jìn)行從發(fā)展經(jīng)濟到社會公共事務(wù)管理的轉(zhuǎn)變,如社區(qū)共建,社區(qū)注重聯(lián)系居民,按時發(fā)放居民社會保障補助。模仿城市居民組織選舉,積極發(fā)展社區(qū)聯(lián)系居民的機制,定期社區(qū)黨員走入貧困家庭,進(jìn)行一定的扶持。再者,社區(qū)居委會面臨“村改居”后原來農(nóng)村集體財產(chǎn)的安置,社區(qū)居民的就業(yè)以及權(quán)益保障等問題,從現(xiàn)實來看,這些問題涉及了原來村民直接的利益,處理這些問題更加的棘手。“村改居”后的社區(qū)居委會面臨新的考驗。第二,居民與居委會關(guān)系的逐漸轉(zhuǎn)變。相比從前,村委會由于對“有關(guān)集體土地的使用、鄉(xiāng)村事務(wù)的管理、征繳稅費及鄉(xiāng)村整體發(fā)展的決策,都與他們的利益息息相關(guān)”[3]。可以看出,村民和村委會之間相互聯(lián)系更頻繁,村民對村委會更具有依賴性。“村改居”后,由于社區(qū)居委會職能的逐漸轉(zhuǎn)變,更多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環(huán)境衛(wèi)生,文藝活動,計劃生育等事務(wù)上來,社區(qū)與居民的經(jīng)濟利益關(guān)系削弱,并且社會保障的社會化,使居民與社會有了更多的聯(lián)系,居民對居委會的聯(lián)系逐漸稀松,依賴性變小。
二、“村改居”社區(qū)治理的困境
(一)社區(qū)居委會行政化色彩偏重
“村改居”社區(qū)是農(nóng)村社區(qū)向城市社區(qū)的過渡階段,這些社區(qū)行政化色彩偏重,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村改居”社區(qū)被納入城市居委會后,管理體制行政科層化,居委會人員的任職條件等都由街道確定,很多事情唯街道辦馬首是瞻。以前村委會財政由集體經(jīng)濟承擔(dān),但是進(jìn)入城市轉(zhuǎn)制以后,由街道撥付,并且經(jīng)費減少,造成社區(qū)有事時經(jīng)費拿不來的困境,還要向街道上級部門申請經(jīng)費,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區(qū)對街道的依賴。第二,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政府的職能部門經(jīng)常把任務(wù)推給街道,但“下任務(wù)不下權(quán)”、“下事情不下錢”[4]。以前的村委會基本出面協(xié)調(diào)本村的大小事務(wù),基本顧忌到每個人的利益,但是在城市中,社區(qū)轉(zhuǎn)變了角色,充當(dāng)了服務(wù)者的角色,上級政府職能部門把任務(wù)委派給街道,街道下放任務(wù),把社區(qū)作為自己的派出機構(gòu),社區(qū)成了上級部門的“一條腿”,把引導(dǎo)變成了指導(dǎo)。社區(qū)疲于應(yīng)付上級任務(wù),而忘記了自己服務(wù)的功能。
(二)居民參與不足,社區(qū)自治能力不強
現(xiàn)在“村改居”社區(qū)治理中,行政化效應(yīng)仍然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社區(qū)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意識淡薄,社區(qū)動員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區(qū)自治的能力。撤村后,雖然村民在戶籍身份上變?yōu)槌鞘芯用瘢瑓s因為缺少新的聯(lián)系紐帶而出現(xiàn)疏離化的傾向,這樣更加需要新的組織載體對其進(jìn)行服務(wù)和管理。同時,外村人及外地人口作為城市新的人口群體,打破了原來農(nóng)村的“半熟人”社會。這些社區(qū)居民離開了原來的村落,脫離了原來的村委會的管理,對現(xiàn)在的社區(qū)缺乏認(rèn)同感。多數(shù)村民進(jìn)入城市后,有事還是會找原來的村干部,很多村民“居”在社區(qū)中,而非“生活”在社區(qū)中。在心理上還沒有完全接受現(xiàn)有的“村改居”社區(qū)治理模式。當(dāng)問到你關(guān)心社區(qū)的事情嗎?大多村民認(rèn)為沒什么事情找社區(qū)干什么,平時也很少關(guān)心社區(qū)的事情,社區(qū)工作人員有事叫就去,沒事就不去社區(qū)。大多數(shù)“村改居”的居民政治的參與意識強烈,可是政治參與行為不高。除此之外,“社區(qū)治理是基層多元利益主體進(jìn)行集體行動和選擇的過程,社區(qū)治理需要協(xié)調(diào)多方的利益與關(guān)系,現(xiàn)代社區(qū)分化為功能各異的各類現(xiàn)代社會組織,與傳統(tǒng)社區(qū)相比具有高度的分化性。”[5]受主客觀影響,“村改居”社區(qū)居民對現(xiàn)有社區(qū)共同利益關(guān)心較少,缺乏認(rèn)同感和歸屬感,社區(qū)的很多活動都是由賦閑在家的老年人參加,年輕人都忙于工作,社區(qū)成立的一些協(xié)會或者興趣小組都是和老年人有關(guān),對于年輕人來說,社區(qū)由于經(jīng)費等問題,難以開展活動吸引年輕人的眼球。社區(qū)由于參與主體的局限性,再加上居民參與意識不強,導(dǎo)致社區(qū)自治能力不強。
(三)社區(qū)自治組織發(fā)展相對緩慢
當(dāng)前“村改居”社區(qū)自組織的發(fā)展面臨一些困境。“村改居”后的居民主要由原來的失地農(nóng)民組成,39.7%的調(diào)查對象文化程度是在“初中及以下”,有29.3%的調(diào)查對象文化程度為“高中(中專、中技)[6],這些居民大多是年歲較大的老人,文化程度普遍低,對于社區(qū)規(guī)章制度也不是很了解,缺乏參與社區(qū)事務(wù)的前提和動力,目前是阻礙社區(qū)自組織發(fā)展的主要障礙。大多數(shù)“村改居”居民在受訪中談到,社區(qū)的事務(wù)自己也搞不懂,按章辦事就行。再者,“村改居”后,大量外來人口涌入社區(qū),對社區(qū)事務(wù)關(guān)注度不高。“村改居”的社區(qū)居民發(fā)展自組織也只是局限于有共同愛好的一群人,他們組織興趣協(xié)會,文化活動,但這些自組織沒有制定相關(guān)的組織制度,人員編排,主要是靠熟人社會間的情感維系,情感的維系具有很大的易變性,如果情感有所波動,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成員對組織的參與。
三、解決“村改居”社區(qū)困境的路徑
(一)逐步理清“村改居”社區(qū)居民委員會與政府的關(guān)系
當(dāng)前,許多城市社區(qū)和街道辦事處的關(guān)系處于被領(lǐng)導(dǎo)和領(lǐng)導(dǎo)的一種關(guān)系,“村改居”社區(qū)效仿城市社區(qū)的運行機制,直接承擔(dān)上級指派的任務(wù)。按照“政事分開、政社分開”的原則,理順政府與社區(qū)的關(guān)系。社區(qū)居委會協(xié)助,配合上級政府管理社區(qū)事務(wù),不是一級行政機關(guān),其主要的職能是行使社區(qū)居民賦予的自治權(quán),為社區(qū)居民服務(wù),應(yīng)進(jìn)一步理順基層政府、街道辦事處和社區(qū)的關(guān)系,可以嘗試在基層政府與社區(qū)之間建立一種委托―“式契約關(guān)系[7]。政府作為上級領(lǐng)導(dǎo),對社區(qū)事務(wù)應(yīng)該是給予指導(dǎo)、協(xié)調(diào)、動員、監(jiān)督的功能,在財力物力上給予相應(yīng)的財政支持,而不是參與干涉社區(qū)事務(wù)。社區(qū)居委會作為其人,按照上級指示完成各項工作,以此有效地推進(jìn)兩者平等合作的關(guān)系,除此之外,社區(qū)作為自治的載體,應(yīng)該改良方法,廣開渠道,積極配合,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創(chuàng)造好的條件,并且讓居民感受到自我管理,自我服務(wù)的甜頭,關(guān)乎社區(qū)重大事件時,可以召開居民聽證會,制定相關(guān)制度來提高工作的透明度,使居民參與到社區(qū)管理之中。社區(qū)居委會不再是上級政府的“一條腿”,而是幫助上級政府更好地進(jìn)行基層治理。
(二)建立社區(qū)居民參與的制度規(guī)范,逐漸完善居民自治
隨著我國基層民主的發(fā)展,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居民參與的一系列問題,比如參與方式,參與對象等,加快建設(shè)“村改居”居民參與的建設(shè),在“村改居”后,需要建立社區(qū)居民參與的長效機制,必須用制度來明確不同參與主體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再者,方便提供便捷的參與渠道,各個“村改居”社區(qū)根據(jù)本社區(qū)的實際狀況,制定詳細(xì)的參與程序,讓居民一目了然。
“實行居民自治,制度建設(shè)是根本”[8]。也就是說要加強居民自治的制度保障,居民可以直接或者間接進(jìn)行居委會選舉,居民會議主要進(jìn)行決策議事,由居民集體討論的自治章程為主作為民主管理制度,準(zhǔn)時無誤地公布社區(qū)重大事務(wù),向居民公開的民主監(jiān)督制度。這樣做,可以使居民有了制度的保證,也給居民自治提供了一個標(biāo)準(zhǔn)。在對“村改居”的居民進(jìn)行采訪時,居民們認(rèn)為居民有權(quán)力選舉居委會班子,對此他們表示很滿意,對于整個選舉過程,大多數(shù)居民認(rèn)為選舉過程還是比較公正的,認(rèn)為通過選舉可以選出好的領(lǐng)導(dǎo)。
(三)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
“國家太大,社會成員之間不可能建立面對面協(xié)調(diào)機制,社區(qū)較小,居民之間可以而且事實上存在面對面協(xié)調(diào)機制;市場信奉‘沒有免費的午餐’,市場不信眼淚,而社區(qū)提倡鄰里互助,關(guān)愛弱勢群體。”由此看來,社區(qū)自組織是國家和市場的補充,在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發(fā)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社區(qū)自組織優(yōu)于“被組織”,在自組織環(huán)境下,社區(qū)居民的生活關(guān)聯(lián)度,熟悉程度都比較高,它內(nèi)在的規(guī)范能夠讓居民無形的自組織起來,降低了社區(qū)治理的成本。如何實現(xiàn)社區(qū)治理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需要社區(qū)外力的支持,同樣也需要社區(qū)居民自組織對社區(qū)內(nèi)部事務(wù)的整合配置,從而實現(xiàn)社區(qū)的“善治”。目前,“村改居”社區(qū)最主要的自組織是社區(qū)居委會。許多居民自發(fā)組織形式多樣的協(xié)會,可以不僅豐富生活,而且為社區(qū)居民之間的交往提供了一個平臺。社區(qū)自組織和社區(qū)治理的目標(biāo)是相一致的,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是為社區(qū)治理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提供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大力培育發(fā)展社區(qū)自組織是衡量社區(qū)治理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biāo)。
參考文獻(xiàn):
[1]代帆.中國城鎮(zhèn)化發(fā)展的地區(qū)差異及與經(jīng)濟增長的關(guān)系研究[D].北京:首都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2011.
[2]高靈芝,胡旭昌.城市邊緣地帶“村改居”后“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濟南市的調(diào)查[J].重慶社會科學(xué),2005(9).
[3]羅伯特?貝涅威克,朱迪?豪威爾.社區(qū)自治:村委會與居委會的初步比較[J].城市管理,2003(1).
[4]郭榮茂,許斗斗.關(guān)注村改居后失地農(nóng)民就業(yè)保障問題[J].發(fā)展研究,2007(3).
[5]藍(lán)宇蘊:都市里的村莊――一個“新村社共同體”的實地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5.
[6]唐亞林,陳先書.社區(qū)自治:城市社會基層民主的復(fù)歸與張揚[J].學(xué)術(shù)界,2003(3).
篇2
關(guān)鍵詞:民族村寨旅游;社區(qū)參與;困境;治理路徑
中圖分類號:F590.75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C文章編號:0439-8114(2011)11-2354-04
The Dilemma and Governance Path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LIAO Jun-h(huán)ua1,2
(1.Guizhou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Guiyang 550025,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 of community residents and increasing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s the key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 tourism.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cessity and dilemma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the ways of increasing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dilemma; governance path
隨著我國西部民族地區(qū)旅游業(yè)的發(fā)展,當(dāng)?shù)刎S富的原生態(tài)自然和文化遺產(chǎn)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nèi)外旅游者。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云南、貴州、四川、廣西等地相繼以開發(fā)民族文化村寨、民族農(nóng)家樂、生態(tài)博物館等多種形式,逐步發(fā)展起民族村寨旅游活動,走出了一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旅游發(fā)展道路[1]。民族村寨旅游的發(fā)展既讓當(dāng)?shù)厣鐓^(qū)居民脫貧致富,又很好地傳承和保護(hù)了民族文化,產(chǎn)生了良好的經(jīng)濟和社會文化效應(yīng)。然而,由于諸多條件的限制,在民族村寨旅游發(fā)展過程中,社區(qū)參與出現(xiàn)了許多困境,主要表現(xiàn)在居民參與和利益分配問題上。總體來看,不同開發(fā)模式、不同發(fā)展階段下的民族村寨旅游,社區(qū)參與不足成為瓶頸性問題[2],導(dǎo)致民族村寨旅游的深度發(fā)展陷入困境,制約了其可持續(xù)性。因此,關(guān)注社區(qū)居民的利益,提高其旅游參與度,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fā)展的關(guān)鍵。
1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綜述
國外學(xué)者較早地對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進(jìn)行了研究,1985年墨菲首次在旅游研究中引入了社區(qū)參與的概念,在《旅游:社區(qū)方法》一書中提出了“社區(qū)參與”的概念,開始嘗試從社區(qū)參與的視角研究和把握旅游。他在該書中闡述了旅游業(yè)對社區(qū)的影響和社區(qū)的旅游參與,探討了如何從社區(qū)角度開發(fā)和規(guī)劃旅游的問題。他的方法強調(diào)社區(qū)居民參與規(guī)劃和決策的制定過程,目的在于通過當(dāng)?shù)鼐用竦膮⑴c規(guī)劃,減少居民對旅游的抵觸和沖突,以便更好地參與旅游活動[3]。此后,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研究越來越受到學(xué)者的重視。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社區(qū)參與旅游的研究進(jìn)一步增多,國際著名旅游學(xué)術(shù)刊物《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都開辦了專輯對社區(qū)參與旅游進(jìn)行討論,使相關(guān)研究不斷向前推進(jìn)。1997年6月,世界旅游組織、世界旅游理事會與地球理事會聯(lián)合頒布了《關(guān)于旅游業(yè)的21世紀(jì)議程》,該義程明確提出,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旅游業(yè)必須保證社區(qū)成員,包括婦女和當(dāng)?shù)厝耍寄芟硎苈糜嗡鶐淼囊嫣帯_@是在旅游業(yè)的官方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將社區(qū)居民作為關(guān)懷對象,并把社區(qū)居民參與旅游發(fā)展當(dāng)作旅游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過程中一項重要內(nèi)容和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國外社區(qū)參與旅游研究在20世紀(jì)70~80年代間成為旅游學(xué)科的熱點。主要涉及社區(qū)參與的類型、社區(qū)參與旅游的措施、社區(qū)居民與旅游發(fā)展的利益關(guān)系、社區(qū)在旅游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
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為尋求可持續(xù)的旅游發(fā)展途徑,中國學(xué)者開始研究旅游目的地社區(qū)參與旅游的問題,在理論與實踐上研究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問題。國內(nèi)學(xué)者目前主要是從社區(qū)參與的民主性、內(nèi)涵性和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障礙、旅游規(guī)劃過程、利益公平化、問題解決對策等幾個方面進(jìn)行了研究[4-8]。總體而言,國內(nèi)關(guān)于社區(qū)參與旅游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關(guān)于社區(qū)參與旅游方面的研究偏重于理論和宏觀的研究,缺乏深入細(xì)致的實證研究,且多數(shù)研究是在西方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反應(yīng)性的分析,局限于西方的理論分析框架和思路,研究方法比較單一。真正從中國社會文化特點及中國國情出發(fā)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比較匱乏。
2社區(qū)參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必要性
2.1社區(qū)參與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
《關(guān)于旅游業(yè)的21世紀(jì)議程》將“可持續(xù)旅游發(fā)展”明確定義為“在保護(hù)和增強未來機會的同時滿足現(xiàn)時旅游者和東道區(qū)域的需要”,“可持續(xù)旅游產(chǎn)品”是“與當(dāng)?shù)丨h(huán)境、社區(qū)和文化保持一致的產(chǎn)品”。可見,考慮社區(qū)因素是實現(xiàn)旅游業(yè)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之一[5]。社區(qū)參與民族村寨旅游,有利于居民獲得相應(yīng)的利益訴求,以積極的態(tài)度支持旅游業(yè)的發(fā)展,從而促進(jìn)社區(qū)居民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fā)展。因此,社區(qū)參與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
2.2社區(qū)參與是民族村寨居民增加收入的有效途徑
旅游業(yè)是關(guān)聯(lián)度強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旅游業(yè)可以提供大量直接或間接的就業(yè)機會,具有較高的乘數(shù)效應(yīng)。在欠發(fā)達(dá)的民族地區(qū),發(fā)展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增加村民的收入,是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但是,如果發(fā)展中有大量外地人進(jìn)入?yún)⑴c到旅游開發(fā)當(dāng)中,就會使當(dāng)?shù)夭糠致糜问杖胪ㄟ^工資或商業(yè)利潤等方式流出社區(qū),出現(xiàn)旅游漏損現(xiàn)象,使貧困地區(qū)成為“旅游飛地”,削弱旅游乘數(shù)效應(yīng)。事實證明,這樣的地區(qū)往往是經(jīng)濟欠發(fā)達(dá)地區(qū)[9]。而社區(qū)居民參與旅游開發(fā),可減少外地人進(jìn)入的機會,從而相應(yīng)減少旅游漏損,有利于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的發(fā)展。
2.3社區(qū)參與是提高旅游產(chǎn)品質(zhì)量的關(guān)鍵因素
旅游者要獲得滿意的旅游經(jīng)歷,高質(zhì)量的旅游產(chǎn)品是關(guān)鍵。對旅游者而言,高質(zhì)量大致可歸結(jié)為3個方面:設(shè)施的舒適性、體驗的真實性和心理的滿足感[10]。民族地區(qū)旅游獨特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文旅游資源,對游客具有強大的吸引力,而游客體驗的真實性是旅游產(chǎn)品質(zhì)量高低的關(guān)鍵所在。少數(shù)民族居民是民族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傳承者,他們理解本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和深厚的內(nèi)涵,知道哪些民族文化可以作為旅游資源開發(fā)。社區(qū)參與能使旅游開發(fā)符合當(dāng)?shù)氐囊庠负湍芰Γ瑥亩@得居民的支持,有利于社區(qū)居民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fā)展。民族村寨的居民既是旅游的參與者,其本身又是珍貴的旅游資源,他們參與到旅游服務(wù)中,體現(xiàn)了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使游客能體驗到高質(zhì)量的旅游經(jīng)歷。因此,社區(qū)參與是提高民族村寨旅游產(chǎn)品質(zhì)量的關(guān)鍵因素。
2.4社區(qū)參與是旅游資源和環(huán)境保護(hù)的有力保障
旅游業(yè)并非人們所說的無煙工業(yè),在發(fā)展過程中也會帶來諸多負(fù)面影響。近些年來,我國民族地區(qū)旅游業(yè)發(fā)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同時也伴隨著相當(dāng)?shù)呢?fù)面影響,許多貧困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因發(fā)展旅游業(yè)而遭到了較大的破壞[11],民族文化出現(xiàn)漢化、西化和庸俗化的傾向。通過社區(qū)參與旅游,村寨居民可從中獲得豐厚的經(jīng)濟回報,居民逐漸認(rèn)識到旅游業(yè)對他們生存的重要性。而旅游資源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是旅游業(yè)發(fā)展的基礎(chǔ)。因此,社區(qū)居民會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重視對資源和環(huán)境的保護(hù),并且表現(xiàn)在具體行動上。他們在參與旅游規(guī)劃時,會對環(huán)境質(zhì)量、游客容量等問題給予關(guān)注,并自覺監(jiān)督旅游企業(yè)和旅游者的環(huán)保行為。在日常經(jīng)營過程中,居民會身體力行地努力保護(hù)旅游資源和環(huán)境,他們還會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影響旅游者。所有這些舉動對于旅游資源和環(huán)境的保護(hù)無疑是相當(dāng)重要的。
3社區(qū)參與民族村寨旅游的困境
3.1自身意識淡薄的障礙
由于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崇尚權(quán)威和官本位等思想的影響,農(nóng)村居民習(xí)慣于接受集權(quán)式管理模式,對權(quán)勢產(chǎn)生依附心理。由于社會、自然、歷史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生活在偏遠(yuǎn)落后地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居民思想觀念還比較落后,民主意識淡薄,參與意識不強。另外,經(jīng)濟的落后使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居民首先關(guān)心的是生存問題,因為在基本的物質(zh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時,誰也不會對涉及長遠(yuǎn)的發(fā)展規(guī)劃等問題感興趣,更談不上對旅游發(fā)展進(jìn)行投資等活動[4]。村寨居民自身參與意識的淡薄嚴(yán)重阻礙了其參與旅游的程度。
3.2相關(guān)部門忽視的障礙
在我國旅游開發(fā)的實踐中,當(dāng)?shù)鼐用竦拇嬖谕缓鲆暎淅嬖V求沒有得到滿足。政府或公司在旅游參與中往往是強勢群體,是占主導(dǎo)地位的利益主體。而社區(qū)居民是旅游業(yè)的相關(guān)者,占次要地位。目前,我國政府極力推行的旅游扶貧戰(zhàn)略已經(jīng)從主觀上增加了社區(qū)居民參與旅游發(fā)展的因素,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社區(qū)居民作為旅游發(fā)展的主體的地位還沒有得到體現(xiàn),而常常是外來投資商成為主體。由于政府相關(guān)部門的忽視,當(dāng)?shù)鼐用駨穆糜沃械貌坏较鄳?yīng)的利益,他們對發(fā)展旅游就不會支持甚至是反對。
3.3體制與機制的障礙
旅游發(fā)展機制主要包括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保障機制、科學(xué)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提高參與能力的培訓(xùn)機制等。健全的機制是影響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旅游發(fā)展過程中,只有完善的參與機制,才能激勵和保證社區(qū)居民全面參與旅游活動。然而,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在我國還不成熟,機制有待完善,對于相對落后的民族地區(qū)更是如此。在立法方面,國內(nèi)還沒有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來規(guī)定社區(qū)居民應(yīng)如何參與規(guī)劃,以及如何保障社區(qū)居民參與規(guī)劃的有效性,也沒有社區(qū)居民利益保障的相關(guān)制度。體制和機制的缺乏導(dǎo)致社區(qū)居民在參與旅游上障礙重重。
4提高社區(qū)參與度的路徑
4.1建立社區(qū)參與的保障機制是前提
在社區(qū)主要利益相關(guān)者中(旅游企業(yè)、政府和社區(qū)居民),社區(qū)居民處于弱勢地位,利益訴求得不到較好的實現(xiàn)。如果在民族村寨旅游開發(fā)過程中過多地依賴市場機制的運作,旅游業(yè)對欠發(fā)達(dá)地區(qū)的扶助和發(fā)展機會的創(chuàng)造將難以實現(xiàn),導(dǎo)致社區(qū)居民往往被排除在利益主體之外,被邊緣化,達(dá)不到社區(qū)居民與村寨旅游和諧發(fā)展的目的。國內(nèi)外旅游發(fā)展的實踐證明,凡是實行政府主導(dǎo)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國家或地區(qū)旅游業(yè)就發(fā)展快、效益好[12]。因此,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發(fā)展村寨旅游的過程中,應(yīng)發(fā)揮政府的主導(dǎo)作用,建立社區(qū)參與的保障機制,完善社區(qū)參與自治體系,實現(xiàn)社區(qū)的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jiān)督,從制度和機制上保障社區(qū)居民參與民族村寨旅游,努力提高居民參與旅游的程度,這是提高社區(qū)參與程度的前提。
4.2建立科學(xué)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基礎(chǔ)
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整體落后,發(fā)展旅游的資金和技術(shù)匱乏,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往往通過招商引資來開發(fā)旅游資源,造成旅游資源被開發(fā)商控制,從而使社區(qū)居民的利益受損,導(dǎo)致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積極性被削弱,降低了他們支持旅游的熱情,甚至產(chǎn)生敵對情緒,影響了旅游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因此,必須建立科學(xué)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確保居民的利益訴求得到保證,只有這樣才能贏得他們對旅游的了解和支持。可以從為社區(qū)居民提供就業(yè)和參與旅游分紅等方面予以考慮。讓居民真正成為社區(qū)旅游發(fā)展的主人,從利益分配機制上加以保障,促進(jìn)社區(qū)居民和民族村寨旅游的和諧發(fā)展。因此,建立科學(xué)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提高社區(qū)參與程度的基礎(chǔ)。
4.3提高居民素質(zhì)和參與能力是關(guān)鍵
大多數(shù)民族村寨居民由于長期身處貧困落后地區(qū),文化知識水平有限,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淡薄,參與能力較弱,制約了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深度。因此,應(yīng)重視對社區(qū)居民的培訓(xùn)和教育,努力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zhì)。首先,對社區(qū)居民進(jìn)行旅游相關(guān)知識教育,讓他們認(rèn)識旅游,了解旅游業(yè)所帶來的經(jīng)濟利益、社會利益和環(huán)境影響,感受到旅游給自己帶來的切身利益,從而激發(fā)社區(qū)居民參與旅游的興趣和熱情。其次,要讓社區(qū)居民全面參與到村寨旅游發(fā)展中來,就必須提高他們的管理水平和參與能力。只有這樣居民才能真正成為社區(qū)的主人,才能在旅游中獲得應(yīng)有的利益訴求。努力提高居民素質(zhì)和參與能力是增強社區(qū)參與度的關(guān)鍵因素。
4.4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qū)參與是動力
社區(qū)居民參與民族村寨旅游除了保障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和提高其素質(zhì)和參與能力外,外部力量的推動是當(dāng)前民族村寨旅游發(fā)展過程中不可或缺少的強大動力。能夠起推動作用的外部力量主要是非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也稱為民間組織、社會中介組織或第三部門,它是與政府、營利組織(即企業(yè))相對應(yīng)的非營利組織,主要致力于社會服務(wù)和管理[8]。在民族地區(qū)發(fā)展村寨旅游的過程中,由于政府和市場作用的局限性,非政府組織活動空間很大。國外的非政府組織在旅游發(fā)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國目前還缺乏這種非政府組織,這對處于弱勢的民族村寨居民是一種缺憾。因此,在民族村寨社區(qū),要加強非政府組織在旅游發(fā)展過程中的作用,從而促進(jìn)社區(qū)居民參與旅游。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qū)參與是提高社區(qū)參與度的強大動力和保障。
5結(jié)語
社區(qū)參與旅游是民族村寨旅游和諧發(fā)展的必要條件。然而,社區(qū)參與旅游還面臨諸多困境,尤其是在經(jīng)濟落后的民族地區(qū),由于居民自身知識水平和素質(zhì)低下以及體制與機制不完善,其參與旅游的能力還比較弱。因此,需要建立社區(qū)參與的保障機制和科學(xué)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及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社區(qū)參與,同時采取措施努力提高居民參與村寨旅游發(fā)展的能力。只有這樣,民族村寨旅游才能和諧發(fā)展。
參考文獻(xiàn):
[1] 徐永志.民俗風(fēng)情: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著力點[J].旅游學(xué)刊,2006(3):10.
[2] 肖富群.居民社區(qū)參與的動力機制分析[J].廣西社會科學(xué),2004,107(5):161-163.
[3] 孫九霞,保繼剛.從缺失到凸顯: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研究脈絡(luò)[J].旅游學(xué)刊,2006(7):63-68.
[4] 劉緯華.關(guān)于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的若干理論思考[J].旅游學(xué)刊, 2000(1):47-52.
[5] 黎潔,趙西萍.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理論的若干經(jīng)濟學(xué)質(zhì)疑[J].旅游學(xué)刊,2001(4):44-47.
[6] 孫九霞.社區(qū)參與旅游發(fā)展研究的理論透視[J].廣東技術(shù)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2005(5):89-92.
[7] 羅永常.鄉(xiāng)村旅游社區(qū)參與研究――以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郎德村為例[J].貴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自然科學(xué)版),2005(4):108-111.
[8] 劉益,陳烈.旅游扶貧及其開發(fā)模式研究[J]. 熱帶地理,2004(4):396-400.
[9] 林紅.對“旅游扶貧”論的思考[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xué)院學(xué)報,2000(5):49-53.
[10] 王春雷, 周宵. 從人類學(xué)視角探析區(qū)域旅游規(guī)劃的社區(qū)參與[J]. 規(guī)劃師,2003,19(3):71-73.
篇3
【關(guān)鍵詞】社區(qū)治理 利益相關(guān)者 集體行動困境 多元合作
一、問題何以出現(xiàn)――集體行動的合作困境
任何時候,只要許多個人共同使用一種稀缺資源,就會造成環(huán)境的惡化。正如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xué)》中所說,“凡是屬于最多數(shù)人的公共事務(wù)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顧的事物,人們關(guān)懷著自己的所有,而忽視公共的事物;對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對他個人多少有些相關(guān)事物”。即在集體行動中,人們往往選擇趨利避害,對與自己利益相關(guān)或一致的政策做出反應(yīng)。當(dāng)許多人有共同的利益時,當(dāng)他們有一個目的或目標(biāo)時,個人的無組織行動根本不能促進(jìn)共同利益,或根本不能充分個人利益。奧爾森從經(jīng)濟學(xué)的個人主義視角出發(fā),首先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顯著特征就是行為前要進(jìn)行成本收益的計算和權(quán)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目的。中國古代“三個和尚沒水喝”、“濫竽充數(shù)”的故事,俗話中的“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眾口難調(diào)”,實際上也是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
二、治理何以失靈――利益相關(guān)者的角色迷失
社區(qū)的公共事務(wù)不是某個家庭某個個人的簡單需求,而是涉及社區(qū)利益相關(guān)者的共同利益和需求滿足的復(fù)雜過程。因此,在利益相關(guān)者的復(fù)雜博弈中,如何增進(jìn)共識,消除分歧,使各方主體合作互動,在面對“任何時候只要許多人共同使用一種資源,便會發(fā)生環(huán)境的退化”的“公地悲劇”時走出困境,建立合作機制保證利益共享。
社區(qū)治理行政化傾向是現(xiàn)階段中國社區(qū)治理的顯著特征。強國家―弱社會特征的影響下,我國城市社區(qū)管理主要是政府主導(dǎo)。政府過度的進(jìn)入社區(qū)自治事務(wù)中,存在角色越位,造成社區(qū)管理委員會等社區(qū)自治組織在社區(qū)治理中無法發(fā)揮應(yīng)有的作用,限制其發(fā)展。在一些本應(yīng)由政府解決的問題上,政府存在責(zé)任推諉,把本應(yīng)由政府承擔(dān)的職責(zé)推給社區(qū)自治組織,而社區(qū)自治組織又沒由足夠的承接能力,影響了治理的效率。在社區(qū)委員會委員的產(chǎn)生中,存在者低素質(zhì)者當(dāng)選的現(xiàn)象。推選出的代表民意的委員沒有經(jīng)過全體社區(qū)成員的投票選舉,大多數(shù)委員只是對社區(qū)事務(wù)熱心的社區(qū)居民,專業(yè)化程度和素質(zhì)不高。
三、治理路徑何以選擇――多元主體合作治理
1、從“劃槳”到“掌舵”,轉(zhuǎn)變政府角色
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好的事。在當(dāng)前市場經(jīng)濟的體制下,政府不是唯一的權(quán)力中心。目前我國社區(qū)治理中存在嚴(yán)重的行政化傾向,政府將本應(yīng)由其承擔(dān)的職責(zé)轉(zhuǎn)移給社區(qū)基層委員會,而基層的承接力不足,資源資金條件有限,造成在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的管理中角色缺位,錯位。構(gòu)建服務(wù)型政府,法治政府,制定相關(guān)法律規(guī)則規(guī)定政府在社區(qū)事務(wù)中的職責(zé),轉(zhuǎn)變政府由“劃槳”轉(zhuǎn)為“掌舵”的角色,對社區(qū)的良性發(fā)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2、加強社區(qū)自治組織的自治性,提高專業(yè)化水平和規(guī)則意識
社區(qū)自治組織是社區(qū)發(fā)展的重要支撐,在社區(qū)治理中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目前我國的社區(qū)自治組織發(fā)展還很緩慢并長期存在合法性危機,信任缺失,資金資源缺乏等困境,嚴(yán)重影響了社區(qū)自治組織在社區(qū)治理中作用的發(fā)揮。因此,有必要在社區(qū)組織內(nèi)部形成一整套組織運行體系,通過制度規(guī)則避免 “搭便車”現(xiàn)象,促進(jìn)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的治理。建立社區(qū)自治組織與政府的良性互動機制。政府提供給社區(qū)自治組織其缺乏的資金和資源,改變過去政府直接控制社區(qū)的局面,增強社區(qū)自治組織的自主性和靈活性,讓社區(qū)自治組織成為居民意志表達(dá)的代言人。
3、提升參與意識,構(gòu)建社區(qū)居民參與合作機制。
公民個體作為理性人,必然會對參與收益成本進(jìn)行計算。公民個體投入了時間、精力參與社區(qū)事務(wù),能否實現(xiàn)利益訴求,投入成本與預(yù)期回報是否成比例,這些都直接影響著公民個體參與的積極性。當(dāng)公民個體利益與社區(qū)公共利益存在沖突時,社區(qū)公民較多的是從自身利益出發(fā),與自己利益有關(guān)時,參與社區(qū)事務(wù)的熱情就高,反之則低。社區(qū)公共利益與公民個體利益的矛盾導(dǎo)致部分公民直接選擇“搭便車”,而不是積極主動地去參與。在社區(qū)中,應(yīng)強化社區(qū)居民的共同體意識,培養(yǎng)社區(qū)居民的公共精神,構(gòu)建參與合作機制,讓社區(qū)居民積極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wù)的管理中。
參考文獻(xiàn):
[1]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wù)的治理之道[M].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2]衛(wèi)志民.中國城市協(xié)同治理模式的構(gòu)建與創(chuàng)新[J].中國行政管理,2014(3).
[3]陳炳輝.“社區(qū)再造”的原則與戰(zhàn)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區(qū)治理模式[J].行政論壇,2010(3).
[4]李慧鳳.社區(qū)治理與社會管理體制創(chuàng)新――基于寧波市社區(qū)的案例研究[J]. 公共管理學(xué)報,2010(1).
篇4
各區(qū)、縣委,市委各部委,市級國家機關(guān)各黨組,市屬各局、總公司、高等院校黨委,各人民團(tuán)體黨組,各區(qū)縣財政局:
經(jīng)研究決定,適當(dāng)調(diào)整去世離休干部無工作配偶生活困難補助費標(biāo)準(zhǔn),現(xiàn)將有關(guān)事項通知如下:
一、補助標(biāo)準(zhǔn):去世離休干部配偶無工作、有子女的生活困難補助費調(diào)整到每人每月290元;去世離休干部配偶無工作、無子女的生活困難補助費調(diào)整到每人每月435元。
二、執(zhí)行時間:自2000年7月1日起按上述標(biāo)準(zhǔn)執(zhí)行。
三、所需經(jīng)費按原渠道開支。
篇5
[關(guān)鍵詞]社區(qū)治理;公民參與;參與現(xiàn)狀
一、問題背景
十之后全國各地以社區(qū)為突破口,紛紛進(jìn)行創(chuàng)新社區(qū)治理的社區(qū)改革,要破解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困境,優(yōu)化社區(qū)治理能力,就必須更深入準(zhǔn)確的把握社區(qū)治理中公民參與的現(xiàn)狀。我國社會學(xué)者潘小娟將“社區(qū)”定義為:“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nèi)人群組成的、具有相關(guān)利益和內(nèi)在互動關(guān)系的地域性社會生活共同體”[1]。社區(qū)作為社會治理最基層的單元,很多資源、問題、矛盾都積聚在此。在社區(qū)治理改革的背景之下,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廣度和深度究竟如何,這必須進(jìn)行全面而深入的實地調(diào)研才能深化認(rèn)識,從而更好地以改革促動成效。
二、秦淮區(qū)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現(xiàn)狀概況問卷調(diào)查
(一)秦淮區(qū)概況
秦淮區(qū)地處南京主城東南,是南京市四個主城區(qū)之一,區(qū)域面積49.11平方公里,區(qū)域戶籍人口71.62萬人,常住人口103.2萬人,轄五老村、洪武路、大光路等12個街道,106個社區(qū)、6個行政村,1個省級開發(fā)區(qū)――白下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園區(qū)。2012年3月,南京市秦淮區(qū)被民政部批準(zhǔn)確定為首批“全國社區(qū)管理和服務(wù)創(chuàng)新實驗區(qū)”[2]。秦淮區(qū)打造的“中心制―耦合型”社區(qū)治理模式,以主體重塑、多元互動、共建分享為目標(biāo)積極推動了街道社區(qū)綜合體制機制改革,逐漸形成了社區(qū)治理的“秦淮模式”。秦淮區(qū)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的視角下大刀闊斧銳意改革,構(gòu)建了新的社區(qū)治理模式,很多做法值得借鑒和提倡,但是社區(qū)治理的改革究竟對社區(qū)中公民參與產(chǎn)生了多少影響,仍未可知,因此本文通過問卷和訪談對秦淮區(qū)社區(qū)公民參與現(xiàn)狀進(jìn)行深入調(diào)研。
(二)秦淮區(qū)的調(diào)查問卷及分析
本次問卷調(diào)查共發(fā)放問卷200份,回收問卷共計200份,回收率100%。對回收問卷進(jìn)行初步篩選并去除廢卷9份,有效問卷191份,有效回收率為95.5%。經(jīng)過問卷數(shù)據(jù)的初步統(tǒng)計和分析,可以從三個維度了解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狀。調(diào)查對象基本情況(N=191),從被調(diào)查對象基本情況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得知,被調(diào)查者年齡主要集中在25―44歲之間,占總?cè)藬?shù)的50%,18-24歲的被調(diào)查者占10%,44-55歲的被調(diào)查者占16.7%,55歲以上的占23.3%。在選取被調(diào)查對象時,傾向于男女?dāng)?shù)量相近,女性占總數(shù)的53.3%,男性公民占46.7%。從受教育程度來看,本科和中專或高中占被調(diào)查對象的多數(shù),46.7%的被調(diào)查對象受過本科教育,這也是與被調(diào)查對象趨向高知化、年輕化的現(xiàn)象相符的。本調(diào)查對象中66.7%是本地人口,另外居住在本地超過5年的比例是53.3%,這與本小區(qū)地理位置、周邊企業(yè)、學(xué)校環(huán)境有關(guān),不少住戶是租住于此,或因拆遷在此過渡住家。社區(qū)居民對社區(qū)治理體制了解情況(N=191),在針對社區(qū)居民對我國現(xiàn)在社區(qū)治理體制相關(guān)情況的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認(rèn)為社區(qū)居委會不是自治組織的被調(diào)查對象比例竟然高達(dá)56.7%,另外有30%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并且被調(diào)查對象中的70%居民表示自己沒有參加過選舉,這與我國歷來社區(qū)選舉出現(xiàn)的高投票現(xiàn)象相違背,其中有過投票經(jīng)歷的受訪者中有仍有55.5%的人表示是在社區(qū)居民的要求下或社區(qū)鄰居和他人的帶領(lǐng)下參與的投票。
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態(tài)度測量(N=191),在對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態(tài)度測量中,26.7%的受訪者表示在社區(qū)聯(lián)名反映和自身利益無直接相關(guān)的問題時會參加,60%的受訪者表示會視情況而定,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尤其是當(dāng)自身不是直接利益主體。在社區(qū)舉辦活動的參與積極性上,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有高達(dá)83.3的居民只有在宣傳動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參與社區(qū)活動,常常積極主動參加的只占6.7%,甚至有10%的受訪者表示即使動員自己也不會參加。關(guān)于您希望在社區(qū)事務(wù)的決策過程中發(fā)表自己的意見嗎?這一問題,有66.7%的受訪者持肯定態(tài)度,說明居民希望在社區(qū)事務(wù)中自己的意見能夠被大家知曉,甚至得以采納,但仍有33.3%的受訪者表示無所謂。
三、秦淮區(qū)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現(xiàn)狀分析
從問卷調(diào)查及社區(qū)訪談的反饋結(jié)果進(jìn)行分析可以看出現(xiàn)代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現(xiàn)狀的縮影:(一)社區(qū)治理理念的宣傳不夠,動員不足[3]。從維度一、維度二的統(tǒng)計結(jié)果可以看到。受訪對象有60%受過高等教育,但這60%的受訪對象并未體現(xiàn)出有較高的參與熱情,并且他們對社區(qū)治理的體制及現(xiàn)狀并不了解,其中高達(dá)81%的人不知道社區(qū)居委會是自治組織。可見社區(qū)治理中居民對社區(qū)性質(zhì)認(rèn)識不清。即使在整個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的大背景下多元主體協(xié)同治理的宣傳在學(xué)界、政界都有大篇幅的宣傳,但在社區(qū)居民中對此的感受度并不強。在社區(qū)治理過程中應(yīng)該加強理念和基本概念的深化,從意識上和實踐上同步提升。(二)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意識不強,信心不足。從維度一、維度三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可知,60%受過高等教育的受訪者在談及不參加社區(qū)活動的原因時有31%的人表示沒有時間,15%的人認(rèn)為自己的參與與否對社區(qū)治理影響不大,在社區(qū)治理中社區(qū)居民缺乏參與意識,并且參與信心不足,造成參與廣度不夠。在社區(qū)治理存在兩種消極的現(xiàn)象:一是部分民眾在前期有積極的參與意識,但在參與行為受阻或維權(quán)失敗后變趨向于消極被動參與;另一種是本身就沒有較強的參與意識,在被動的參與氛圍中越來越消極。目前在社區(qū)治理中應(yīng)充分調(diào)動維護(hù)這兩部分群體的參與意識和參與熱情。(三)公民參與機制的聯(lián)動性不足。民生工作站機制的創(chuàng)建已三年,雖然取得了諸多成效,但是民眾的知曉率不高,只有5%的受訪群眾表示非常熟悉。同時在社區(qū)治理中不難發(fā)現(xiàn)一個問題,各個社區(qū)、街道在進(jìn)行創(chuàng)新組織設(shè)置的探索中,并不斷有新的創(chuàng)新項目上馬,便會形成新的組織資源的傾斜。在社區(qū)治理中因工作人員有限、工作精力有限、政府績效考核標(biāo)準(zhǔn)等諸多原因,多項參與機制的聯(lián)動存在困難,也就為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多渠道化帶來困境。
四、結(jié)語
新時期我國社區(qū)治理中公民參與困境產(chǎn)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民自身和參與環(huán)境的因素都不容忽視。一方面大的治理改革背景需要公民參與的提高,同時公民參與意識的不斷覺醒和現(xiàn)有參與水平的限制也觸動了公民參與模式的改革,在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的大背景下,要從多個方面來提升社區(qū)公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為國家整體治理水平的現(xiàn)代化奠定基礎(chǔ),就必須深化了解社區(qū)公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狀,從而對癥下藥,才能破解參與困境。
參考文獻(xiàn)
[1]潘小娟.中國基層社會重構(gòu)一社區(qū)治理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2]夏曉麗.城市社區(qū)治理中的公民參與問題研究.博士畢業(yè)論文.山東大學(xué)政治學(xué)理論,2011
[3]顏曉峰.總體國家安全觀引領(lǐng)國家安全治理價值[J].決策與信息,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