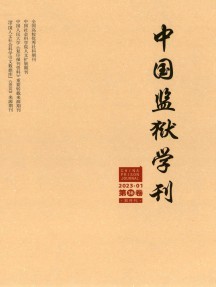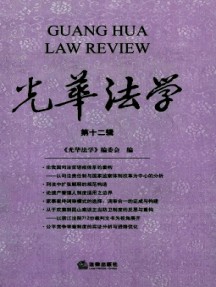刑事責(zé)任能力解釋精選(五篇)
發(fā)布時(shí)間:2023-09-20 09:46:27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shí)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我們?yōu)槟鷾?zhǔn)備了不同風(fēng)格的5篇刑事責(zé)任能力解釋,期待它們能激發(fā)您的靈感。

篇1
論文關(guān)鍵詞:共同犯罪主體;刑事責(zé)任能力;共同犯罪的成立;犯罪論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據(jù)報(bào)道,2007年l0月8日,黃某等三名小學(xué)生在高速公路立交橋上向過往行駛車輛投擲石塊。石塊從立交橋上落下,擊穿一輛剛好駛過的轎車的前擋風(fēng)玻璃,并致乘坐該車的王某死亡。但是,并不能確定是三人中的哪一人丟出的石塊導(dǎo)致慘禍。鑒于三行為人為未成年人,法院認(rèn)定三人為共同危險(xiǎn)行為人,其六名監(jiān)護(hù)人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因而并沒有追究三人的刑事責(zé)任。對(duì)于這一判決當(dāng)無疑義,可若是我們將該案例稍加改變,則會(huì)出現(xiàn)不同的結(jié)局,即(設(shè)例J)如果三名致害人中,有一人是已滿十八周歲的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這三人是否構(gòu)成共同犯罪?如果認(rèn)為構(gòu)成,理由何在?這其實(shí)就是構(gòu)成共同犯罪的主體是否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問題。
二、質(zhì)疑通說
(一)通說主張
關(guān)于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通說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是二人以上,同時(shí),對(duì)于自然人都必須達(dá)到刑事責(zé)任年齡、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依照通說,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與不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共同實(shí)施危害行為的不構(gòu)成共同犯罪,而只能要么無法處理,要么將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作為間接正犯處理。
然而,如此處理,不僅會(huì)導(dǎo)致處罰的漏洞,而且也可導(dǎo)致處罰上的不合理。比如說,(設(shè)例2)母親A教唆l2歲的兒子B實(shí)施盜竊行為,若是依照通說,A只能作為盜竊罪的間接正犯,適用刑法第264條的規(guī)定,進(jìn)行處罰。可是,已經(jīng)l2歲的B是有一定程度的意識(shí)和控制能力的人,將其評(píng)價(jià)為工具而將其母評(píng)價(jià)為間接正犯,未免有些牽強(qiáng)。又如,(設(shè)例3)15周歲的C和l9周歲的D共謀并且由C親自實(shí)施搶奪行為,如果認(rèn)為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與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不能構(gòu)成共同犯罪,而若要使有責(zé)任能力的D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前提條件就是其構(gòu)成共同犯罪。那么,堅(jiān)持通說的話,就會(huì)出現(xiàn)無人對(duì)被害人的損失負(fù)責(zé)的現(xiàn)象。這顯然不盡合理。
(二)質(zhì)疑通說
目前,亦有學(xué)者對(duì)此持反對(duì)觀點(diǎn)。有人認(rèn)為,關(guān)于共同犯罪成立的條件,“二人以上,并不要求兩個(gè)人都具備完全的責(zé)任能力。有責(zé)任能力者和限制責(zé)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共同實(shí)行犯罪的,后者按照刑法第18條第3款的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負(fù)刑事責(zé)任,二人以上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有人主張,通常情況下,“二人以上”都是達(dá)到法定年齡、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現(xiàn)實(shí)中存在沒有達(dá)到法定年齡的人與達(dá)到法定年齡的人共同故意實(shí)施符合客觀構(gòu)成要件的違法行為的現(xiàn)象。
對(duì)于這一問題的爭論,從根本上來說,關(guān)涉的是對(duì)“犯罪”一詞的理解。由于“犯罪”一詞有不同的含義,那么“共同犯罪”自然也是有不同含義的。一般來說,所謂犯罪,是指具備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條件的行為。可是,從結(jié)果無價(jià)值的立場(chǎng)來看,犯罪的本質(zhì)是侵害法益,因此可以說,只要是侵害了法益的行為就是具備了犯罪的本質(zhì)。所以,在一定場(chǎng)合下,“犯罪”是指具備了犯罪的客觀要件的行為。如果要求犯罪是指完全符合犯罪構(gòu)成所有要件的行為,有些法律條款就無法理解了。如:我國刑法第124條。該條第一款規(guī)定:“破壞廣播電視設(shè)施、公用電信設(shè)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嚴(yán)重后果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二款規(guī)定:“過失犯前款罪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認(rèn)為犯罪是具備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條件的行為的話,則是要求將該條第二款理解為“過失犯前款故意破壞廣播電視設(shè)施、公用電信設(shè)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顯然是不合適的。所以,對(duì)于該條第二款的理解就應(yīng)當(dāng)是將“過失犯前款罪”中的“罪”理解為僅指符合前款規(guī)定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及其性質(zhì)的行為,而不要求行為人像第一款那樣出于故意。因此,在有些場(chǎng)合下,對(duì)“犯罪”一詞的含義宜理解為具有法益侵害性的符合犯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即可。
在共同犯罪的場(chǎng)合下,若認(rèn)為“犯罪”并不必須是具備了成立犯罪的全部條件的行為,無刑事責(zé)任能力人就可以與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一道,構(gòu)成共同犯罪了。因?yàn)椋瑹o刑事責(zé)任能力人的行為,完全符合犯罪的客觀構(gòu)成要件,雖然由于其無刑事責(zé)任能力而阻卻了有責(zé)性,但他的侵害法益的行為仍不失為“犯罪”。況且,將年齡作為評(píng)價(jià)刑事責(zé)任能力有無的標(biāo)準(zhǔn)之一,從而構(gòu)成有責(zé)性阻卻事由,只是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在法益侵害性這一點(diǎn)上,未成年人未必比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的危害性小。
這樣,本文前述兩個(gè)設(shè)例所出現(xiàn)的尷尬境況便可以得到解決。母親A教唆12歲的兒子B盜竊,由于A并沒有達(dá)到對(duì)B以及整個(gè)犯罪事實(shí)的支配的程度,將其評(píng)價(jià)為間接正犯過于牽強(qiáng)。這種情形是可以將A、B以共同犯罪論處的,盡管B由于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而阻卻有責(zé)性,從而不予定罪處罰,但由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含義僅指符合犯罪客觀構(gòu)成要件,具有法益侵害性即可。那么,A就是盜竊罪的教唆犯,除了適用第264條之外,還適用第29條第一款后段:“教唆不滿l8周歲的人犯罪的,應(yīng)當(dāng)從重處罰。”也就是說作為教唆犯的A受到了比作為間接正犯更嚴(yán)厲的處罰,同時(shí)也解決了架空第29條第1款后段的現(xiàn)象,使得刑法得到了更好的貫徹。同樣,第二個(gè)設(shè)例中,15歲的C和19歲的D構(gòu)成共同犯罪,且為共同正犯,由于C未滿l6周歲,在搶奪罪上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從而阻卻了有責(zé)性,因此不對(duì)其以搶奪罪論處。而D由于和C成立共同犯罪,且不具有違法阻卻事由以及責(zé)任阻卻事由,因此可以按照搶奪罪定罪處罰。至于文章開頭所提到的案例的“改編版”,本文認(rèn)為,三人中有一人已經(jīng)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兩人為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依然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只是,兩個(gè)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阻卻了有責(zé)性。只有首先認(rèn)定成立共同正犯,才能適用部分實(shí)行全部責(zé)任的原則,才能在不能查明因果關(guān)系的情況下,讓三人共同對(duì)結(jié)果負(fù)責(zé),從而僅對(duì)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者以“以危險(xiǎn)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論處。
顯然,通說是希望通過對(duì)共同犯罪的主體要件進(jìn)行限制,從而限制刑法的處罰范圍,然而,事與愿違,這種限制反而將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圍限定得過窄,不利于對(duì)法益的保護(hù)。所以,認(rèn)為共同犯罪成立的條件中的“二人以上”不以均具備刑事責(zé)任能力為必要反而更有利于對(duì)案件的處理和對(duì)法益的保護(hù)。
行文至此,不得不考慮,對(duì)“犯罪”一詞可以有多種含義,是否有前提呢?也就是說,在何種語境之下,才有可能將“犯罪”做多層次、多角度的理解呢?這又涉及到對(duì)犯罪構(gòu)成體系的選擇。
三、階層犯罪構(gòu)成體系的合理之處
我國通說采取平面耦合式的四要件說。該說一般認(rèn)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由犯罪客體、客觀方面、犯罪主體、主觀方面四個(gè)要件。一旦滿足了這四個(gè)要件則構(gòu)成犯罪。反之,只要不具備其中任何一個(gè)犯罪構(gòu)成要件,就不構(gòu)成犯罪。在這樣的犯罪構(gòu)成體系下,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是當(dāng)然不構(gòu)成犯罪的,進(jìn)而更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所以,文中三個(gè)設(shè)例中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均不構(gòu)成共同犯罪,設(shè)例1和設(shè)例3無法處理,設(shè)例2中的A只能作為間接正犯處理,不得對(duì)其從重處罰。這反映出我國通說理論中,四要件式的犯罪構(gòu)成形式判斷與實(shí)質(zhì)評(píng)價(jià)同時(shí)完成。也就是說,四要件緊密關(guān)聯(lián),彼此印證,形成一個(gè)完整的證明體系,從而共同維持著犯罪實(shí)施的整體性。如果行為事實(shí)符合構(gòu)成要件,在理論上就可以得出結(jié)論,說四個(gè)要件的行為可以受到否定的實(shí)質(zhì)評(píng)價(jià),即依據(jù)犯罪構(gòu)成,就可以具體的構(gòu)成要件為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哪些行為具有社會(huì)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yīng)受刑罰處罰的犯罪行為。在司法裁判中,這種“一次性”的過程也是難以完成的,同時(shí)也與思維規(guī)律并不符合,并且使一次評(píng)價(jià)行為承載的使命過多,就會(huì)出現(xiàn)判斷誤差,司法的準(zhǔn)確性則會(huì)相應(yīng)的降低。此其一。
其二,犯罪構(gòu)成理論應(yīng)當(dāng)反映定罪的過程,而平面耦合式的四要件模式并沒有突出地反映出這一過程的推理形式、進(jìn)路,而是更多地具有了靜態(tài)性的特征。那么,由它們組合起來的犯罪事實(shí)在犯罪實(shí)施終了以后就不可能有任何變化,從而使法律推理和論證變得比較困難。以通說立場(chǎng)來處理三個(gè)設(shè)例,結(jié)論不免給人草率的感覺。
而采取階層式犯罪成立理論,尤其是二階層式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則可避免這些問題,并合理地解決問題。我國權(quán)威學(xué)說也是提倡該種犯罪構(gòu)成理論。因?yàn)椋皇牵扇《A層說有利于堅(jiān)持客觀違法性論,即符合客觀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就是具有違法性的行為,行為是否侵犯法益并不以行為人是否具有非難可能性為前提。在上述三個(gè)設(shè)例中,各未成年人對(duì)所犯的罪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但這并不妨礙對(duì)他們行為所導(dǎo)致的法益侵害性的認(rèn)定,從而可以得出他們實(shí)施了具有違法性的行為,因此可以肯定與同案的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構(gòu)成共同犯罪。二是,階層體系是違法性與有責(zé)性處于不同層面,形成了“違法是客觀的,責(zé)任是主觀的”定式。13周歲的人實(shí)施的諸如故意傷害這樣的犯罪行為,是沒有法律依據(jù)地對(duì)他人的身體健康或者是身體機(jī)能實(shí)施了侵害,從客觀上來講,無疑是具有法益侵害性的,但是,不追究其刑事責(zé)任就是因?yàn)槠錇椴痪哂行淌仑?zé)任能力的人,從而阻卻了有責(zé)性。三是,上述的“犯罪一詞有多重含義”,只能在階層體系中可行。在上述三個(gè)設(shè)例中,認(rèn)定未成年人或者說是此類不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構(gòu)成犯罪的目的,并不是為了一定要追究他們的刑事責(zé)任,而是為了妥善地認(rèn)定和處理與他們共同實(shí)施犯罪行為的具有刑事責(zé)任能力的人的責(zé)任。在平面體系中,犯罪是不可能有多種含義的,那么,在如設(shè)例的場(chǎng)合下,很容易造成認(rèn)定的困境。
篇2
關(guān)鍵詞:民事責(zé)任能力 概念分析 法律責(zé)任
從范疇類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應(yīng)屬于主體論范疇。但主體論范疇是對(duì)法律世界的實(shí)踐豐_體和價(jià)值主體及其相互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和概括,既反映誰在從事法律活動(dòng),又說明誰是法律調(diào)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體論范疇。這種落差絕非無意義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筆者認(rèn)為,對(duì)這種差別的追根問底,也許可以找到自然人責(zé)任能力問題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各種定義與評(píng)析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各種定義
目前,我國民法理論界遠(yuǎn)沒就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概念達(dá)成共識(shí)。學(xué)者們’般將《民法通則》133條作為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法源性規(guī)定,在解釋該條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形成多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根據(jù)側(cè)重點(diǎn)不同和出現(xiàn)時(shí)間先后,町分為:(1)廣義民事行為能力說:(2)侵權(quán)行為能力說和不法行為能力說:(3)權(quán)利能力涵蓋說;(4)客觀能力說;(5)獨(dú)立責(zé)任資格說。此外,還有意思能力說、識(shí)別能力說兩種觀點(diǎn),但學(xué)者己對(duì)此達(dá)成共識(shí),認(rèn)為它們是認(rèn)定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標(biāo)準(zhǔn)。
(二)對(duì)以各種定義的評(píng)析
整體而言,廣義行為能力說,侵權(quán)行為能力說和不法行為能力說都是從民事行為能力方面展開的,爭論的不過是立法技術(shù)上枝節(jié)問題。具體而廣義行為能力說僅是學(xué)者理論上的一種概括,并不是要取消嚴(yán)格意義上的行為能力與責(zé)任能力概念的區(qū)分,當(dāng)然,在立法技術(shù)上,這區(qū)分行為能力和責(zé)仟能力實(shí)有必要。①而且,事實(shí)上此說極易混同了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概念,因此難說妥當(dāng)。對(duì)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責(zé)任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兩者雖有聯(lián)系,但二者畢竟兩種不同的資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質(zhì)方面存在明顯區(qū)別。②侵權(quán)利行為能力說或不法行為能力說顯然比廣義行為能力說更科學(xué)。
“權(quán)利能力涵蓋說”雖然在理論上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但這種理論構(gòu)建的意義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樣無力解釋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規(guī)定,于司法實(shí)踐的意義不大;另‘方面其論證過程中沒有明晰民事義務(wù)與民事責(zé)任的界限,難說立論穩(wěn)固;再者用民事權(quán)利能力這種民法學(xué)前提性范疇來界定民事責(zé)任能力,有解構(gòu)般人格權(quán)概念的風(fēng)險(xiǎn),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現(xiàn)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權(quán)的概念。果真如此,這樣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得不償失了。
客觀能力說突破了從主體資格方向解釋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局限,為認(rèn)識(shí)民事責(zé)任能力提供了一條新思路,提示人們?cè)谘芯棵袷仑?zé)任能力問題應(yīng)注意民事責(zé)任的財(cái)產(chǎn)客觀性,不宜過于強(qiáng)調(diào)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觀判斷引向客觀判斷,把價(jià)值判斷變?yōu)槭聦?shí)判斷。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至少在方法論卜此說是有重要意義的。但”客觀能力說”將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將主體資格物化為的自然人的財(cái)產(chǎn):能力,顯然混淆了民事責(zé)任和民事責(zé)任能力兩個(gè)概念。
獨(dú)立責(zé)任資格說沒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邏輯上最為完整。遺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沒有在此概念的基礎(chǔ)上展開,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數(shù)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認(rèn)為,此說雖然強(qiáng)調(diào)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獨(dú)立地位,對(duì)以意思能力和識(shí)別能力之判斷標(biāo)準(zhǔn)提出正確的質(zhì)疑。
到此,我們可以對(duì)以上爭論進(jìn)行梳理與簡化:(1)學(xué)者們大致在兩個(gè)層次論說民事責(zé)任能力,第一種是討論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辦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解釋成為法律的例外規(guī)定,筆者將此稱為廣義的民事責(zé)任能力:第二種是直接討論了限制行為能力和無行為能力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即直接用責(zé)任能力作為不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理由,對(duì)于完全行為能力人,他們認(rèn)為是無意義的,因?yàn)樗腥硕加胸?zé)任能力。(2)學(xué)者們認(rèn)為: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與民事行為能力問題緊密聯(lián)系,因?yàn)橹挥邢扔忻袷滦袨椴艜?huì)有所謂的民事責(zé)任問題,但是立法上應(yīng)分立而是整合存學(xué)者們有分歧。第一個(gè)問題實(shí)際上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視角選擇問題,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會(huì)產(chǎn)生異議,就研究視角的選擇,本文是在廣義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上立論的;第二個(gè)問題實(shí)際上是立法技術(shù)問題,只需考證實(shí)在法規(guī)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說這是個(gè)立法價(jià)值選擇問題。
二、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邏輯分析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縱向邏輯關(guān)系
民事責(zé)任能力在縱向的邏輯構(gòu)成大致為法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能力。法律責(zé)任概念在我國的法理學(xué)界仍有爭議,但張文顯教授的觀點(diǎn)已被大多數(shù)學(xué)者接受。他認(rèn)為,法律責(zé)任是”法律責(zé)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權(quán)利或違反法定義務(wù)而引起的,由于專門機(jī)關(guān)認(rèn)定并歸結(jié)于法律關(guān)系的有責(zé)主體的,帶有直接強(qiáng)制性的義務(wù),即由于違反第一性法定義務(wù)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義務(wù)。”③很明顯,此概念更多是根據(jù)刑事責(zé)任和行政責(zé)任抽象而得出的。對(duì)此,有學(xué)者批評(píng)此說”有些籠統(tǒng)”,并進(jìn)一步修正認(rèn)為法律責(zé)任是”是指由于違背了具有法律意義的義務(wù)或基于特定的法律關(guān)系,有責(zé)主體應(yīng)受譴責(zé)而必須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負(fù)擔(dān)”。④至少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確。
依《民法通則》第106條規(guī)定,民事責(zé)任的來源方式三:其一,為違反合間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wù);其二,為凼過錯(cuò)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cái)產(chǎn),侵害他人財(cái)產(chǎn)、人身的;其三,雖沒有過錯(cuò),但法律規(guī)定的。即,民事責(zé)任的來源可簡稱為違約、侵權(quán)和法律規(guī)定。而民事責(zé)任的本質(zhì),梁慧星教授概括為:(1)民事責(zé)任為法律關(guān)系的構(gòu)成要素;(2)民事責(zé)任使民事權(quán)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責(zé)任是連結(jié)民事權(quán)利與國家公權(quán)力之中介;(4)民事責(zé)任為一種特別債。
通過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縱向邏輯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論:(1)既然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都具有國家保證的強(qiáng)制性,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也應(yīng)是法定的,屬民法強(qiáng)行性規(guī)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權(quán)利,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目的也應(yīng)是保障權(quán)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應(yīng)在被保護(hù)之列。(3)既然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是屬于客觀的制度事實(shí),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至少不能為一個(gè)抽象的主觀標(biāo)準(zhǔn),否則可能會(huì)導(dǎo)致民事責(zé)任形同虛設(shè)。
篇3
關(guān)鍵詞:民事責(zé)任能力概念分析法律責(zé)任
從范疇類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應(yīng)屬于主體論范疇。但主體論范疇是對(duì)法律世界的實(shí)踐豐_體和價(jià)值主體及其相互關(guān)系的認(rèn)識(shí)和概括,既反映誰在從事法律活動(dòng),又說明誰是法律調(diào)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體論范疇。這種落差絕非無意義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筆者認(rèn)為,對(duì)這種差別的追根問底,也許可以找到自然人責(zé)任能力問題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各種定義與評(píng)析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各種定義
目前,我國民法理論界遠(yuǎn)沒就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概念達(dá)成共識(shí)。學(xué)者們’般將《民法通則》133條作為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法源性規(guī)定,在解釋該條規(guī)定的基礎(chǔ)上形成多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根據(jù)側(cè)重點(diǎn)不同和出現(xiàn)時(shí)間先后,町分為:(1)廣義民事行為能力說:(2)侵權(quán)行為能力說和不法行為能力說:(3)權(quán)利能力涵蓋說;(4)客觀能力說;(5)獨(dú)立責(zé)任資格說。此外,還有意思能力說、識(shí)別能力說兩種觀點(diǎn),但學(xué)者己對(duì)此達(dá)成共識(shí),認(rèn)為它們是認(rèn)定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標(biāo)準(zhǔn)。
(二)對(duì)以各種定義的評(píng)析
整體而言,廣義行為能力說,侵權(quán)行為能力說和不法行為能力說都是從民事行為能力方面展開的,爭論的不過是立法技術(shù)上枝節(jié)問題。具體而廣義行為能力說僅是學(xué)者理論上的一種概括,并不是要取消嚴(yán)格意義上的行為能力與責(zé)任能力概念的區(qū)分,當(dāng)然,在立法技術(shù)上,這區(qū)分行為能力和責(zé)仟能力實(shí)有必要。①而且,事實(shí)上此說極易混同了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的概念,因此難說妥當(dāng)。對(duì)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責(zé)任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兩者雖有聯(lián)系,但二者畢竟兩種不同的資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質(zhì)方面存在明顯區(qū)別。②侵權(quán)利行為能力說或不法行為能力說顯然比廣義行為能力說更科學(xué)。
“權(quán)利能力涵蓋說”雖然在理論上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但這種理論構(gòu)建的意義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樣無力解釋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規(guī)定,于司法實(shí)踐的意義不大;另‘方面其論證過程中沒有明晰民事義務(wù)與民事責(zé)任的界限,難說立論穩(wěn)固;再者用民事權(quán)利能力這種民法學(xué)前提性范疇來界定民事責(zé)任能力,有解構(gòu)般人格權(quán)概念的風(fēng)險(xiǎn),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現(xiàn)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權(quán)的概念。果真如此,這樣的理論創(chuàng)新就得不償失了。
客觀能力說突破了從主體資格方向解釋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局限,為認(rèn)識(shí)民事責(zé)任能力提供了一條新思路,提示人們?cè)谘芯棵袷仑?zé)任能力問題應(yīng)注意民事責(zé)任的財(cái)產(chǎn)客觀性,不宜過于強(qiáng)調(diào)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觀判斷引向客觀判斷,把價(jià)值判斷變?yōu)槭聦?shí)判斷。應(yīng)當(dāng)承認(rèn),至少在方法論卜此說是有重要意義的。但”客觀能力說”將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將主體資格物化為的自然人的財(cái)產(chǎn):能力,顯然混淆了民事責(zé)任和民事責(zé)任能力兩個(gè)概念。
獨(dú)立責(zé)任資格說沒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邏輯上最為完整。遺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沒有在此概念的基礎(chǔ)上展開,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數(shù)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認(rèn)為,此說雖然強(qiáng)調(diào)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獨(dú)立地位,對(duì)以意思能力和識(shí)別能力之判斷標(biāo)準(zhǔn)提出正確的質(zhì)疑。
到此,我們可以對(duì)以上爭論進(jìn)行梳理與簡化:(1)學(xué)者們大致在兩個(gè)層次論說民事責(zé)任能力,第一種是討論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限制行為能力人和無行為能辦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解釋成為法律的例外規(guī)定,筆者將此稱為廣義的民事責(zé)任能力:第二種是直接討論了限制行為能力和無行為能力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即直接用責(zé)任能力作為不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理由,對(duì)于完全行為能力人,他們認(rèn)為是無意義的,因?yàn)樗腥硕加胸?zé)任能力。(2)學(xué)者們認(rèn)為: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與民事行為能力問題緊密聯(lián)系,因?yàn)橹挥邢扔忻袷滦袨椴艜?huì)有所謂的民事責(zé)任問題,但是立法上應(yīng)分立而是整合存學(xué)者們有分歧。第一個(gè)問題實(shí)際上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視角選擇問題,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會(huì)產(chǎn)生異議,就研究視角的選擇,本文是在廣義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上立論的;第二個(gè)問題實(shí)際上是立法技術(shù)問題,只需考證實(shí)在法規(guī)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說這是個(gè)立法價(jià)值選擇問題。
二、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邏輯分析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縱向邏輯關(guān)系
民事責(zé)任能力在縱向的邏輯構(gòu)成大致為法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能力。法律責(zé)任概念在我國的法理學(xué)界仍有爭議,但張文顯教授的觀點(diǎn)已被大多數(shù)學(xué)者接受。他認(rèn)為,法律責(zé)任是”法律責(zé)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權(quán)利或違反法定義務(wù)而引起的,由于專門機(jī)關(guān)認(rèn)定并歸結(jié)于法律關(guān)系的有責(zé)主體的,帶有直接強(qiáng)制性的義務(wù),即由于違反第一性法定義務(wù)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義務(wù)。”③很明顯,此概念更多是根據(jù)刑事責(zé)任和行政責(zé)任抽象而得出的。對(duì)此,有學(xué)者批評(píng)此說”有些籠統(tǒng)”,并進(jìn)一步修正認(rèn)為法律責(zé)任是”是指由于違背了具有法律意義的義務(wù)或基于特定的法律關(guān)系,有責(zé)主體應(yīng)受譴責(zé)而必須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負(fù)擔(dān)”。④至少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確。
依《民法通則》第106條規(guī)定,民事責(zé)任的來源方式三:其一,為違反合間或者不履行其他義務(wù);其二,為凼過錯(cuò)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cái)產(chǎn),侵害他人財(cái)產(chǎn)、人身的;其三,雖沒有過錯(cuò),但法律規(guī)定的。即,民事責(zé)任的來源可簡稱為違約、侵權(quán)和法律規(guī)定。而民事責(zé)任的本質(zhì),梁慧星教授概括為:(1)民事責(zé)任為法律關(guān)系的構(gòu)成要素;(2)民事責(zé)任使民事權(quán)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責(zé)任是連結(jié)民事權(quán)利與國家公權(quán)力之中介;(4)民事責(zé)任為一種特別債。
通過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縱向邏輯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論:(1)既然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都具有國家保證的強(qiáng)制性,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也應(yīng)是法定的,屬民法強(qiáng)行性規(guī)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權(quán)利,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的目的也應(yīng)是保障權(quán)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應(yīng)在被保護(hù)之列。(3)既然民事責(zé)任及法律責(zé)任是屬于客觀的制度事實(shí),那么民事責(zé)任能力至少不能為一個(gè)抽象的主觀標(biāo)準(zhǔn),否則可能會(huì)導(dǎo)致民事責(zé)任形同虛設(shè)。
(二)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橫向邏輯關(guān)系
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橫向邏輯關(guān)系為民事權(quán)利能力、民事行為能力及民事責(zé)任能力。相對(duì)于法律責(zé)任和民事責(zé)任是可在實(shí)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實(shí),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則為學(xué)者們的抽象,在此我們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國民法的理論構(gòu)成。德國民法理論認(rèn)為,一般來說,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指”成為權(quán)利和義務(wù)載體的能力”。梅迪庫斯指出這是從消極意義理解權(quán)利能力的,拉倫茲進(jìn)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權(quán)利主體資格意義在于確定通過行使[權(quán)利]所獲得的利益歸屬于權(quán)利主體。⑥而德國民法理論認(rèn)為,民事行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備了行為能力,即可能通過自己的意思表示構(gòu)建法律關(guān)系。但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能力卻鮮有正面論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國《民法典》過于重視對(duì)財(cái)產(chǎn)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以至于除姓名權(quán)規(guī)定在總則里外,其他人格權(quán)都規(guī)定在債法的侵權(quán)行為之中。所以,德國學(xué)者認(rèn)為這是個(gè)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如梅迪庫斯就認(rèn)為:”在義務(wù)方面,此類[即確定義務(wù)主體(筆者注)疑慮很少發(fā)生。雖然無行為能力人必須通過其他人來履行自己的義務(wù),但是,一旦確定了義務(wù)人,同時(shí)也就確定了對(duì)不履行義務(wù)承擔(dān)責(zé)任的財(cái)產(chǎn)。就這一點(diǎn)而言,孩子負(fù)有義務(wù)還是父母負(fù)有義務(wù),是一個(gè)具有實(shí)質(zhì)性區(qū)別的問題”。
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權(quán)利能力關(guān)系,我國民法理論界并無分歧,通說認(rèn)為:民事權(quán)利能力是一種最基本的民事能力,無民事權(quán)利能力即無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談不上有無民事行為能力,更談不上有無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問題。而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關(guān)系,對(duì)于完全民事行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爭議,前諸多種爭議均是對(duì)于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和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不同看法而產(chǎn)生的。
這樣的規(guī)定凸顯了我國民法以民事法律關(guān)系調(diào)整對(duì)象的”靜”地規(guī)制模式的邏輯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則》第54條和第55條相當(dāng)于給自然人的行為設(shè)置一般性守法義務(wù),既不合理,也不經(jīng)濟(jì):其結(jié)果是使《民法通則》第106條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一般規(guī)定的成了特別規(guī)定;另一方面,其邏輯結(jié)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責(zé)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則》第133條成了極難理解的例外規(guī)定之例外。換句話說,無論采廣義行為能力說,還是狹義行為能力說都將無法解釋民事責(zé)任來源。
通過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橫向邏輯結(jié)構(gòu)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I)將廣義的行為能力限定為法律意義上的行為能力本是立法技術(shù)的產(chǎn)物為各國通例,而限制程度為立法選擇也無可厚非。但如果我們把第54條和第55條看作立法技術(shù)的產(chǎn)物而不宜傷筋動(dòng)骨的話。那么,第106條將責(zé)任能力與廣義的行為能力聯(lián)系起來實(shí)非恰當(dāng),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條和第55條的范圍,否則就會(huì)得出在非法行為中要么有責(zé)任能力負(fù)擔(dān)不利后果要么有行為能力(狹義)免責(zé)的奇怪結(jié)論。(2)既然民事行為能力(狹義)與民事責(zé)任能力在實(shí)在法意義上并無關(guān)聯(lián),那么我國《民法通則》在民事責(zé)任法方面的統(tǒng)一規(guī)定之”統(tǒng)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為民事責(zé)任法的基礎(chǔ)概念民事責(zé)任能力,我們或許可能在法理意義上”統(tǒng)一民事責(zé)任法。
三、民事責(zé)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論文將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概念界定為:民事責(zé)任能力,指民事主體據(jù)以獨(dú)立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資格,為民事責(zé)任法規(guī)范中的屬人因素,其意義在于確定負(fù)法律上”必須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wù)人。筆者認(rèn)為,從法律規(guī)范層面定義民事責(zé)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幾個(gè)優(yōu)點(diǎn):
一、用”資格”和”法律地位”來定義”能力”,相對(duì)于用”能力”來定義”能力”更具邏輯上的準(zhǔn)確性,從而使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權(quán)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獨(dú)立起來。按凱爾森的觀點(diǎn),如考察責(zé)任負(fù)擔(dān)人的法律地位,當(dāng)規(guī)范將某個(gè)人的行為當(dāng)作法律條件或法律資格時(shí),意思是,只有這個(gè)人才有能力,個(gè)有”能力”作為或不作為這一行為,只有他才有”資格”(為competence,最廣義的資格)。
篇4
內(nèi)容提要: 一方面,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quán)責(zé)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權(quán)責(zé)任都適用民事責(zé)任能力。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應(yīng)以責(zé)任的發(fā)生原因如侵權(quán)行為、違約行為等為界定標(biāo)準(zhǔn),而應(yīng)以歸責(zé)原則為界定標(biāo)準(zhǔn),即僅適用于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事責(zé)任,不適用于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能力在本質(zhì)上是過錯(cuò)能力,是致害人的行為構(gòu)成過錯(cuò)行為的法律前提,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是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配套設(shè)施”。我國現(xiàn)行法中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存在諸多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民事責(zé)任能力是民法上的一個(gè)重要概念。我國民法學(xué)者對(duì)這一概念存在理解上的分歧,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不法行為能力說”和“侵權(quán)行為能力說”。前者認(rèn)為,民事責(zé)任能力既包括當(dāng)事人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的能力,也包括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和其他民事責(zé)任的能力。[1]后者認(rèn)為,民事責(zé)任能力僅包括當(dāng)事人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的能力,不涉及其他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2]之所以發(fā)生這樣的爭議,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學(xué)者們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存在不同的見解;另一方面,學(xué)者們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本質(zhì)缺乏準(zhǔn)確的認(rèn)識(shí)。有鑒于此,筆者將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予以考察,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行反思并探討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本質(zhì)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以下簡稱《侵權(quán)責(zé)任法》)相關(guān)條款的完善。
一、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quán)責(zé)任:以其他民事責(zé)任為考察中心
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首先需要探討如下問題:民事責(zé)任能力是否適用于侵權(quán)責(zé)任以外的其他民事責(zé)任?由于民事責(zé)任能力解決的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精神病人、癡呆癥人及其他心智能力有障礙的人)是否需要對(duì)其致害行為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之問題,因此上述問題也可以表述為如下兩個(gè)更為具體的問題:一是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及其他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二是在無因管理和不當(dāng)?shù)美樾沃校闯赡耆撕途裾系K者是否需要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
對(duì)于第一個(gè)問題,我國有學(xué)者認(rèn)為,民事行為能力或者說締約能力本身就包含了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的能力,當(dāng)事人如果不具備相應(yīng)的民事行為能力,合同就不能生效,從而就談不上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是否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屬于締約能力解決的問題,既然民法已經(jīng)對(duì)締約能力作了明確規(guī)定,就沒有必要再規(guī)定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的能力。[3]筆者認(rèn)為,這種觀點(diǎn)欠妥。締約能力并不能完全覆蓋違約責(zé)任能力。不具備締約能力的人也有可能成為有效合同的當(dāng)事人從而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此時(shí)就需要考察其是否具備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的能力。例如,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由法定人代其訂立合同成為合同當(dāng)事人,若未按合同要求履行債務(wù),就需要確定由誰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對(duì)此,需要區(qū)分兩種情形:其一,如果違約責(zé)任采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而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被認(rèn)定為不具備足夠的識(shí)別能力從而不構(gòu)成過錯(cuò),那么他不會(huì)因?yàn)樽陨淼男袨椋ㄗ鳛榛虿蛔鳛椋┒袚?dān)違約責(zé)任,[4]不過,他卻需要對(duì)其法定人的過錯(cuò)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這是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qū)民法的通說。根據(jù)《德國民法典》第278條第1句的規(guī)定,債務(wù)人如果是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需要對(duì)其作為履行輔助人的法定人的過錯(cuò)負(fù)責(zé)。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所謂“民法”第224條亦有類似規(guī)定。[5]《瑞士債法》第101條雖然僅規(guī)定債務(wù)人對(duì)其履行輔助人的過錯(cuò)負(fù)責(zé),但很多學(xué)者主張將該條類推適用于法定人之過錯(cuò)。[6]《日本民法典》對(duì)此雖然未作明文規(guī)定,但日本民法通說亦認(rèn)為債務(wù)人須對(duì)其法定人的過錯(cuò)負(fù)責(zé)。[7]在此種情形中,法定人的識(shí)別能力彌補(bǔ)了被監(jiān)護(hù)人識(shí)別能力的不足,使其能夠成為法律行為的當(dāng)事人。其二,如果違約責(zé)任采用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由于責(zé)任的成立不以債務(wù)人的過錯(cuò)為要件,因此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識(shí)別能力的欠缺不妨礙其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由此可見,如果由法定人代為訂立合同,無論采何種歸責(zé)原則,不具備締約能力的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都需要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
無締約能力人成為有效合同的當(dāng)事人并不限于上述情形。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12、13條的規(guī)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經(jīng)其法定人同意即可締結(jié)超出其行為能力限度的合同(法律行為),從而成為該法律行為的債務(wù)人。該債務(wù)原則上應(yīng)由法定人代為履行,此時(shí)法定人如有可歸責(zé)的違反債務(wù)之行為,應(yīng)當(dāng)歸屬于債務(wù)人。如果事實(shí)上是由債務(wù)人自己履行,那么在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下,債務(wù)人當(dāng)然要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下,如果債務(wù)人的行為違反義務(wù),法定人要么因其懈怠、要么因其輕率而具有過錯(cuò),依據(jù)債法上的履行輔助人和法定人過錯(cuò)之歸屬規(guī)則,該過錯(cuò)也應(yīng)該歸屬于債務(wù)人。除此之外,還存在“事后無締約能力”之情形,即某人在訂立合同時(shí)具備相應(yīng)的行為能力,合同生效后因患精神病喪失行為能力。此時(shí),也不能說該當(dāng)事人必然不需要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即便采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其仍然可能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因?yàn)槠湫枰獙?duì)作為法定人的監(jiān)護(hù)人的過錯(cuò)負(fù)責(zé)。當(dāng)然,如果事發(fā)突然,具有監(jiān)護(hù)資格的人不知道債務(wù)人已喪失行為能力從而自己已經(jīng)成為監(jiān)護(hù)人或者雖然知道自己成為監(jiān)護(hù)人但根本不知道被監(jiān)護(hù)人曾與某人訂立合同從而未及時(shí)履行債務(wù),則監(jiān)護(hù)人就沒有過錯(cuò),被監(jiān)護(hù)人無需依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對(duì)其履行遲延負(fù)責(zé)。
總之,締約能力并不能解決所有涉及違約責(zé)任能力的問題,無締約能力人并非一律不承擔(dān)違約責(zé)任。對(duì)于違約責(zé)任以外的其他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締約能力更是鞭長莫及。由此可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需要承擔(dān)以及依據(jù)什么來承擔(dān)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之問題仍然需要一個(gè)有別于締約能力的理論來解決。
對(duì)于第二個(gè)問題,我國有不少學(xué)者認(rèn)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可能承擔(dān)無因管理和不當(dāng)?shù)美?zé)任。[8]筆者認(rèn)為,這種認(rèn)識(shí)也值得商榷。其理由如下:
(1)所謂“不當(dāng)?shù)美?zé)任”是一個(gè)不太精確的表述,它實(shí)際上包含了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和該債務(wù)不履行所產(chǎn)生的責(zé)任。不當(dāng)?shù)美麄鶆?wù)在性質(zhì)上并非民事責(zé)任。因?yàn)椴划?dāng)?shù)美⒉簧婕皩?duì)當(dāng)事人行為的評(píng)價(jià),僅涉及對(duì)客觀利益關(guān)系的考量。它關(guān)注的是“結(jié)果不法”而不是“行為不法”。只要當(dāng)事人的利益存在客觀不法狀況,即本應(yīng)屬于甲的利益無正當(dāng)原因地處于乙的支配之下,就構(gòu)成不當(dāng)?shù)美琜9]受益人就有義務(wù)將所得利益返還于對(duì)方,此為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而非責(zé)任,在法律上也不需要考察受益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cuò)。唯一涉及受益人主觀狀態(tài)的情形是:受益人如果知道其取得利益無正當(dāng)原因,則應(yīng)將其受領(lǐng)時(shí)所得之全部利益或知悉無正當(dāng)原因時(shí)現(xiàn)存之利益及附加利益一并返還;反之,如果不知道其取得利益無正當(dāng)原因且所得利益已不存在者,不負(fù)返還義務(wù)。在理論上,上述兩種情形往往分別被表述為“惡意受領(lǐng)人的返還責(zé)任”與“善意受領(lǐng)人的返還責(zé)任”,[10]或者把前者稱為“加重責(zé)任”。[11]那么,此處所謂的“責(zé)任”究竟是否真正意義上的民事責(zé)任?在學(xué)理層面上,上述對(duì)于善意受益人與惡意受益人區(qū)別對(duì)待的規(guī)則有兩種可能的解釋:其一,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自受益人知道其無正當(dāng)原因受益時(shí)成立。據(jù)此,惡意受益人要么自取得利益時(shí)起成為債務(wù)人,要么自事后知道其取得利益欠缺正當(dāng)原因時(shí)起成為債務(wù)人。無論如何,在惡意受益人成為債務(wù)人后,債務(wù)的標(biāo)的物即為所得利益,若所得利益在此后喪失以至于最終不能返還給受損人時(shí),則構(gòu)成債務(wù)不履行,其需要向受損人支付與所失利益相當(dāng)?shù)膬r(jià)額,此即所謂“加重責(zé)任”,它在性質(zhì)上屬于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不履行之責(zé)任。[12]善意受益人直到受損人向其請(qǐng)求返還不當(dāng)?shù)美麜r(shí)才知其無正當(dāng)原因受益,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也自此時(shí)成立,其范圍自然僅及于現(xiàn)存之利益,因?yàn)閭鶆?wù)的效力不能溯及地發(fā)生,此即所謂“善意受領(lǐng)人的返還責(zé)任”,它在性質(zhì)上屬于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而不是民事責(zé)任。其二,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自受益人獲得利益時(shí)成立。據(jù)此,如果受益人知其無正當(dāng)原因受益而未妥善保管該利益致其喪失,則受益人須負(fù)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此即所謂“加重責(zé)任”。如果受益人直至受損人向其主張權(quán)利時(shí)才知其無正當(dāng)原因受益,此前一直以為自己是該利益的所有人,可對(duì)之為任意處分,即便因保管或使用不慎而致該利益喪失,相對(duì)于受損人也不構(gòu)成過錯(cuò),因?yàn)槭芤嫒瞬⒉恢雷约旱男袨闀?huì)導(dǎo)致他人利益受損害。既然善意受益人對(duì)于利益的喪失無過錯(cuò),則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之下,其對(duì)于“得而復(fù)失”的利益自然不必負(fù)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此即所謂“善意受領(lǐng)人的返還責(zé)任”,它涉及的是善意受益人是否就已喪失的利益承擔(dān)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之問題。顯然,無論對(duì)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的成立采用主觀(知情)主義還是客觀(受益)主義,學(xué)者們所謂的“不當(dāng)?shù)美?zé)任”都可以定性為不當(dāng)?shù)美颠€債務(wù)或者該債務(wù)的不履行責(zé)任。就前者而言,并不涉及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因?yàn)榇藗鶆?wù)并非責(zé)任,即便該債務(wù)的成立取決于債務(wù)人的主觀狀態(tài),該狀態(tài)也不是責(zé)任能力;就后者而言,涉及民事責(zé)任能力問題,但它并非“不當(dāng)?shù)美?zé)任能力”,而是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能力的一種。在民法理論上,關(guān)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應(yīng)承擔(dān)不當(dāng)?shù)美颠€的“加重責(zé)任”,頗有爭議。[13]筆者認(rèn)為,如果將該責(zé)任視為一種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就比較好解釋:若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具備相應(yīng)的責(zé)任能力,則其應(yīng)承擔(dān)“加重責(zé)任”;若其不具備相應(yīng)的責(zé)任能力,則不應(yīng)承擔(dān)“加重責(zé)任”。但是,如果是法定人代其從事交易并發(fā)生給付不當(dāng)?shù)美曳ǘㄈ嗣髦獰o正當(dāng)原因受益,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仍然應(yīng)承擔(dān)“加重責(zé)任”,因?yàn)榉ǘㄈ说闹橐约斑^錯(cuò)歸屬于被人。
(2)無因管理中的責(zé)任也需要作具體分析。在民法學(xué)上,關(guān)于無因管理的性質(zhì)和成立條件有兩種學(xué)說。根據(jù)傳統(tǒng)民法學(xué)上的通說,無因管理在性質(zhì)上屬于準(zhǔn)契約或準(zhǔn)法律行為,因此應(yīng)該準(zhǔn)用民法關(guān)于行為能力之規(guī)定,即要求管理人具備行為能力。此為第一種學(xué)說。根據(jù)當(dāng)代民法學(xué)上的通說,無因管理在性質(zhì)上屬于事實(shí)行為,不要求管理人具備行為能力。此為第二種學(xué)說。[14]若依第一種學(xué)說,則無行為能力人不能成為無因管理人,不需要承擔(dān)無因管理關(guān)系中的民事責(zé)任,限制行為能力人可以實(shí)施與其行為能力相應(yīng)的無因管理并承擔(dān)由此產(chǎn)生的民事責(zé)任———不履行無因管理人的適當(dāng)管理義務(wù)、繼續(xù)管理義務(wù)、[15]財(cái)物返還義務(wù)所產(chǎn)生的責(zé)任。這在性質(zhì)上屬于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若依第二種學(xué)說,則無行為能力人和限制行為能力人均可以成為無因管理人,享有請(qǐng)求本人償還管理費(fèi)用并補(bǔ)償所受損失的權(quán)利。不過,為了保護(hù)欠缺行為能力的無因管理人,《德國民法典》第682條規(guī)定此類管理人僅依照關(guān)于侵權(quán)行為損害賠償和不當(dāng)?shù)美囊?guī)定負(fù)其責(zé)任,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民法學(xué)者大都認(rèn)為應(yīng)借鑒此種立法例。[16]也就是說,民法上關(guān)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欠缺責(zé)任能力的規(guī)定也適用于欠缺行為能力之無因管理人的民事責(zé)任,[17]包括正當(dāng)無因管理關(guān)系中的責(zé)任和不當(dāng)無因管理關(guān)系中的責(zé)任。其中,前者在性質(zhì)上屬于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后者在性質(zhì)上屬于侵權(quán)責(zé)任。[18]可見,關(guān)于無因管理的性質(zhì)和成立條件無論采何種學(xué)說,其所涉及的責(zé)任都是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或侵權(quán)責(zé)任,并非一種獨(dú)立的“無因管理責(zé)任”。
對(duì)以上兩個(gè)問題的考察可以小結(jié)如下:其一,若對(duì)違約責(zé)任采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一律需要自己承擔(dān)責(zé)任,此時(shí),民事責(zé)任能力無用武之地,民事責(zé)任能力之欠缺不能阻卻違約責(zé)任的成立;如果采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那么不具備相應(yīng)識(shí)別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不對(duì)自己的違約行為負(fù)責(zé),因?yàn)樗麄兩胁痪邆錁?gòu)成過錯(cuò)違約行為之能力,但他們通常需要為法定人的過錯(cuò)負(fù)責(zé),除非事發(fā)突然,法定人沒有過錯(cuò),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無須對(duì)此負(fù)責(zé)。其他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亦同。其二,在不當(dāng)?shù)美蜔o因管理關(guān)系中,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可能涉及的責(zé)任在性質(zhì)上要么屬于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要么屬于侵權(quán)責(zé)任,究竟是否承擔(dān)這些責(zé)任需要考察其責(zé)任能力。總之,對(duì)侵權(quán)責(zé)任以外的民事責(zé)任,民事責(zé)任能力有適用之余地。究竟是否適用,取決于該民事責(zé)任采用何種歸責(zé)原則。
二、民事責(zé)任能力適用范圍限于侵權(quán)責(zé)任中的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與例外
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需要承擔(dān)采用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特殊侵權(quán)責(zé)任,取決于無過錯(cuò)侵權(quán)責(zé)任的立法理由。現(xiàn)代各國侵權(quán)法在傳統(tǒng)的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之外,普遍規(guī)定對(duì)某些特殊侵權(quán)責(zé)任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如鐵路事故責(zé)任、機(jī)動(dòng)車事故責(zé)任、環(huán)境污染損害責(zé)任、產(chǎn)品責(zé)任、飼養(yǎng)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等。這些侵權(quán)責(zé)任被視為危險(xiǎn)責(zé)任,其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理論依據(jù)包括原因責(zé)任主義、衡平責(zé)任主義、報(bào)償責(zé)任主義、違法歸責(zé)主義、危險(xiǎn)歸責(zé)主義、多元主義等。[19]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是報(bào)償責(zé)任主義、危險(xiǎn)歸責(zé)主義和多元主義。[20]
《侵權(quán)責(zé)任法》及其他法律也規(guī)定了若干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危險(xiǎn)責(zé)任,除去明顯與未成年人、精神障礙者無關(guān)的外,高度危險(xiǎn)物(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物質(zhì))致害責(zé)任、危險(xiǎn)作業(yè)責(zé)任、飼養(yǎng)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環(huán)境污染致害責(zé)任、在公共道路上遺撒妨礙通行物致害責(zé)任[21]以及機(jī)動(dòng)車交通事故中的部分無過錯(cuò)責(zé)任(10%限度內(nèi))[22]等是否關(guān)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具體分析。
危險(xiǎn)作業(yè)致害責(zé)任、產(chǎn)品責(zé)任、環(huán)境污染致害責(zé)任的主體都是經(jīng)營者,既包括具備法人資格的經(jīng)營者,也包括不具備法人資格的經(jīng)營者,如個(gè)人獨(dú)資企業(yè)、個(gè)體工商戶、合伙企業(yè)等。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有可能因繼承或精神無障礙時(shí)的投資行為而成為企業(yè)主、店主或有限合伙人,若企業(yè)致害,其有可能成為責(zé)任主體。高度危險(xiǎn)物致害責(zé)任的主體是占有人和使用人,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的主體是飼養(yǎng)人和管理人,在公共道路上遺撒妨礙通行物致害責(zé)任的主體是遺撒行為人,機(jī)動(dòng)車交通事故責(zé)任的主體是機(jī)動(dòng)車所有權(quán)人、使用人、盜搶人。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有可能成為所有權(quán)人,那么是否可能成為占有人、使用人、飼養(yǎng)人、管理人、遺撒行為人、盜搶人?現(xiàn)代民法一般不要求占有人具備占有意思,只要占有人對(duì)標(biāo)的物具備事實(shí)上的管領(lǐng)力即可,頂多只要求占有人具備一項(xiàng)無特別品質(zhì)要求的自然的意思,因此占有人不需要具備行為能力。一個(gè)6歲的兒童在大街上撿了一個(gè)錢包也可以成為占有人。[23]若以此占有概念為準(zhǔn),則用硫酸傷人的精神病人即成為危險(xiǎn)物的占有人。除了盜搶、管理之外,飼養(yǎng)、使用、遺撒也可以作類似解釋。
那么,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作為經(jīng)營者、所有權(quán)人、占有人、使用人、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是否需要承擔(dān)無過錯(cuò)之危險(xiǎn)責(zé)任?從危險(xiǎn)責(zé)任的理論依據(jù)來看,若采用報(bào)償責(zé)任主義,則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作為危險(xiǎn)設(shè)施或危險(xiǎn)事業(yè)的經(jīng)營者、所有權(quán)人需要承擔(dān)無過錯(cuò)責(zé)任;而他們作為危險(xiǎn)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動(dòng)物的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若無行為能力則不應(yīng)該承擔(dān)責(zé)任;其作為機(jī)動(dòng)車的所有權(quán)人是否需要承擔(dān)危險(xiǎn)責(zé)任則有疑問,若著眼于損失的轉(zhuǎn)嫁或分散,由于其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似乎不應(yīng)承擔(dān)無過錯(cuò)責(zé)任;同理,其作為危險(xiǎn)物的占有人、使用人、動(dòng)物的飼養(yǎng)人、遺撒行為人,也不應(yīng)承擔(dān)無過錯(cuò)責(zé)任。如果采用多元主義,將報(bào)償責(zé)任主義與所謂的危險(xiǎn)歸責(zé)主義相結(jié)合,則結(jié)論與采用報(bào)償責(zé)任主義時(shí)相同。
從比較法上看,在德國民法學(xué)說和判例中,對(duì)于危險(xiǎn)責(zé)任的成立是否以當(dāng)事人具備責(zé)任能力為前提存在爭議。一般認(rèn)為,危險(xiǎn)責(zé)任不以責(zé)任能力為要件,但機(jī)動(dòng)車保有人、動(dòng)物飼養(yǎng)人身份的認(rèn)定與行為能力有關(guān),欠缺行為能力的人不能成為保有人或飼養(yǎng)人,除非經(jīng)過法定人同意。[24]有學(xué)者認(rèn)為,機(jī)動(dòng)車致害責(zé)任和飼養(yǎng)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適用責(zé)任能力制度,即欠缺責(zé)任能力的人對(duì)其致害不需要承擔(dān)責(zé)任。[25]在瑞士,按照其民法學(xué)通說,無責(zé)任能力(判斷能力)人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如建筑物致害責(zé)任。[26]在荷蘭,按照《荷蘭民法典》第6編第183條的規(guī)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雇主責(zé)任、建筑物致害責(zé)任、經(jīng)營危險(xiǎn)物致害責(zé)任、經(jīng)營礦業(yè)和垃圾場(chǎng)致害責(zé)任、占有危險(xiǎn)動(dòng)產(chǎn)致害責(zé)任、占有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例外的是,如果占有危險(xiǎn)動(dòng)產(chǎn)或動(dòng)物的是未滿14歲的兒童且該動(dòng)產(chǎn)或動(dòng)物并非被用于從事營業(yè)的,則由行使家長權(quán)的父母或由監(jiān)護(hù)人代替該兒童承擔(dān)責(zé)任。[27]在英格蘭和蘇格蘭,16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擁有或占有動(dòng)物,其父母被認(rèn)定為動(dòng)物保有人,從而承擔(dān)責(zé)任。[28]總之,從比較法上看,占主導(dǎo)地位的觀點(diǎn)是: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不以民事責(zé)任能力為法律前提,而危險(xiǎn)物品占有人和動(dòng)物飼養(yǎng)人身份的認(rèn)定通常需要考慮其識(shí)別或判斷能力。
筆者認(rèn)為,比較法上的這種觀點(diǎn)值得借鑒。關(guān)于危險(xiǎn)責(zé)任,如果適用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將導(dǎo)致作為危險(xiǎn)源利益享有者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逃脫其本應(yīng)承擔(dān)的責(zé)任,這顯然背離了構(gòu)建危險(xiǎn)責(zé)任制度的立法目的。為了使占有、使用并非用于從事營業(yè)的危險(xiǎn)物品或動(dòng)物的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免于民事責(zé)任,與其在危險(xiǎn)責(zé)任人的資格(責(zé)任能力)這個(gè)要素上設(shè)置門檻,不如在危險(xiǎn)行為人這個(gè)要素上設(shè)置門檻,即占有、使用、遺撒危險(xiǎn)物及飼養(yǎng)動(dòng)物等行為需要以當(dāng)事人具備必要的識(shí)別或判斷能力為前提。雖然按照現(xiàn)代民法原理,占有、使用、飼養(yǎng)等事實(shí)行為本不要求行為人具備行為能力,但若標(biāo)的物是危險(xiǎn)物可能給行為人帶來責(zé)任負(fù)擔(dān),則另當(dāng)別論。因?yàn)檫@些潛藏著較大風(fēng)險(xiǎn)的事實(shí)行為仍然以行為人具備必要的識(shí)別或判斷能力為法律前提,無行為能力人必定不具備此種能力,不能理性地選擇是否從事這種行為,所以不能承擔(dān)此類危險(xiǎn)責(zé)任。如果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事實(shí)上“占有”危險(xiǎn)物品或動(dòng)物并致人損害,應(yīng)該將其視為一般侵權(quán)行為,適用一般侵權(quán)行為的責(zé)任能力制度,即監(jiān)護(hù)人因失職而負(fù)責(zé)。不過,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作為危險(xiǎn)設(shè)施或危險(xiǎn)事業(yè)的所有權(quán)人還是作為經(jīng)營者,這兩種情況的法律效果存在不同。因?yàn)樗麄儾⒎窃谧R(shí)別能力欠缺的狀態(tài)下自己選擇成為所有權(quán)人或經(jīng)營者的,而是要么通過繼承要么通過先前的、精神健全狀態(tài)下的行為而成為危險(xiǎn)設(shè)施或危險(xiǎn)事業(yè)的所有權(quán)人或經(jīng)營者。對(duì)于后一種情況,監(jiān)護(hù)人作為其人或代管人補(bǔ)足了其能力上的不足,而該設(shè)施或事業(yè)的利益是由自己而非監(jiān)護(hù)人享有的,因此可成為危險(xiǎn)責(zé)任主體,而非由監(jiān)護(hù)人承擔(dān)危險(xiǎn)責(zé)任。在某些情形中,由于未成年人或精神障礙者是以經(jīng)營為目的占有危險(xiǎn)物品,因此應(yīng)該將其認(rèn)定為危險(xiǎn)事業(yè)的經(jīng)營者,使其承擔(dān)不以民事責(zé)任能力為前提的危險(xiǎn)責(zé)任。事實(shí)上,危險(xiǎn)責(zé)任以外的無過錯(cuò)侵權(quán)責(zé)任也存在類似現(xiàn)象。例如,甲是個(gè)體戶,雇了幾個(gè)工人,后來甲患了精神病,但并未停止?fàn)I業(yè),在此期間有個(gè)工人在工作過程中致人損害,甲對(duì)此需要承擔(dān)雇主責(zé)任,不得以自己欠缺民事責(zé)任能力為由不負(fù)賠償責(zé)任。
總之,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但是,他們由于欠缺足夠的識(shí)別能力,因此通常不能成為非用于營業(yè)的危險(xiǎn)物品占有人和動(dòng)物飼養(yǎng)人,也不必承擔(dān)相關(guān)的侵權(quán)責(zé)任。
三、民事責(zé)任能力本質(zhì)之重述:以過錯(cuò)能力為中心
綜上所述,一方面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限于侵權(quán)責(zé)任;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侵權(quán)責(zé)任都適用民事責(zé)任能力。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不應(yīng)該以責(zé)任的發(fā)生原因(如侵權(quán)行為、違約行為等)為標(biāo)準(zhǔn)予以界定,而應(yīng)該以責(zé)任的歸責(zé)原則為標(biāo)準(zhǔn)予以界定,即民事責(zé)任能力僅適用于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事責(zé)任,不適用于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事責(zé)任。從這個(gè)意義上說,前述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能力含義的“侵權(quán)行為能力(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說”不能成立。如果把民事責(zé)任能力理解為侵權(quán)行為能力或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顯然是不適當(dāng)?shù)模诶碚撋蠠o法解決違約責(zé)任及其他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如果其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話)的承擔(dān)問題,這就如同給一個(gè)成年人戴上一頂兒童帽。況且,如果簡單地將民事責(zé)任能力理解為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那么無行為能力人就不具備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從而不需要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包括一般侵權(quán)責(zé)任和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特殊侵權(quán)責(zé)任,這顯然與上述關(guān)于特殊侵權(quán)責(zé)任的考察結(jié)論相矛盾。所謂的“不法行為能力說”也不精確。該學(xué)說試圖以“不法行為能力”這一概念涵蓋民事主體對(duì)侵權(quán)行為、違約行為及其他不法行為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的資格,但卻無法解釋為什么欠缺“不法行為能力”的人仍然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和違約責(zé)任。
無論是“不法行為能力說”,還是“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說”,都停留在民事責(zé)任能力這一概念的表面,沒有揭示其本質(zhì)。筆者認(rèn)為,民事責(zé)任能力是致害人的行為構(gòu)成過錯(cuò)行為的法律前提,在本質(zhì)上是過錯(cuò)能力。只有具備過錯(cuò)能力的致害人的行為才構(gòu)成過錯(cuò)侵權(quán)行為或過錯(cuò)違約行為,依據(jù)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需要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欠缺過錯(cuò)能力的致害人的行為不構(gòu)成過錯(cuò)侵權(quán)行為或過錯(cuò)違約行為,不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或違約責(zé)任,但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或違約責(zé)任,因?yàn)檫@些責(zé)任不以“過錯(cuò)行為”為要件。
“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本質(zhì)是過錯(cuò)能力”這一命題可以從法律史中得到印證。對(duì)法律史的考察表明,民事責(zé)任能力與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密切相關(guān)。凡是采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法,都有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如后期羅馬法以及近現(xiàn)代民法。在后期羅馬法中,7歲以下的未適婚人[29]可以免于私犯(侵權(quán))責(zé)任,7歲以上的未適婚人有些也可以免于私犯責(zé)任。[30]這個(gè)時(shí)期,羅馬法對(duì)于私犯責(zé)任已經(jīng)明確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31]近代民法也是如此。最具代表性的是1794年《普魯士普通邦法》以及1811年《奧地利民法典》。這兩部法典都采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同時(shí)也都要求致害人具備歸責(zé)能力。[32]
與此不同,凡是采用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民法都沒有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如早期羅馬法。在古羅馬早期的《十二表法》中,未適婚人不能免于私犯(侵權(quán))責(zé)任,其心智能力之欠缺只能作為減輕責(zé)任的事由。這一時(shí)期的羅馬法尚未明確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在這方面,中世紀(jì)日耳曼法的立場(chǎng)更為鮮明,其對(duì)侵權(quán)責(zé)任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結(jié)果責(zé)任)。[33]與此相應(yīng),日耳曼法普遍承認(rèn)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需要對(duì)其致害行為負(fù)賠償責(zé)任。同樣,凡是主張侵權(quán)責(zé)任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學(xué)者,也都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持否定態(tài)度,如古典自然法學(xué)家托瑪修斯。按照托瑪修斯的看法,《阿奎利亞法》上的訴權(quán)之所以要求行為人具有過錯(cuò),是因?yàn)樗哂袘土P性。[34]這也決定了該訴權(quán)不能針對(duì)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因?yàn)檫@兩種人毫無疑問是不應(yīng)該受懲罰的。然而,依據(jù)萬民法和自然理性,侵權(quán)訴權(quán)是純粹賠償性的,不具有懲罰性,既可以針對(duì)無過錯(cuò)的行為人也可以針對(duì)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他們雖然沒有故意或過失的能力,但卻有致害的能力,因此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對(duì)其致害行為仍然需要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
很顯然,民事責(zé)任能力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是相生相伴的,前者是后者的“配套設(shè)施”。只要民法采用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就需要判定致害人是否具有過錯(cuò),而構(gòu)成過錯(cuò)則要求致害人對(duì)其行為具有相當(dāng)?shù)淖R(shí)別和理解能力,否則其致害行為就是無過錯(cuò)的。這種能力就是過錯(cuò)能力,我國民法學(xué)者一般稱之為“民事責(zé)任能力”。遺憾的是,恰恰因?yàn)槭褂昧诉@個(gè)不夠精確的術(shù)語,導(dǎo)致我們長期以來未能準(zhǔn)確地認(rèn)識(shí)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本質(zhì),進(jìn)而導(dǎo)致我們?cè)谄淅碚撗芯亢椭贫仍O(shè)計(jì)上出現(xiàn)了諸多偏差。
在德國的民法文獻(xiàn)中,與我們所謂的民事責(zé)任能力相當(dāng)?shù)男g(shù)語主要有三個(gè):Verschuldensfahigkeit(“過錯(cuò)能力”)、Zurechnungsfahigkeit(“歸責(zé)能力”)和Deliktsfahigkeit(“侵權(quán)行為能力”)。[35]目前更常用的術(shù)語是“過錯(cuò)能力”和“歸責(zé)能力”。 [36]而“歸責(zé)能力”也容易陷入與“民事責(zé)任能力”類似的邏輯困境。相較之下,“過錯(cuò)能力”這個(gè)術(shù)語最為精當(dāng)。所謂過錯(cuò)能力,即致害人的主觀狀態(tài)被認(rèn)定為民法上的過錯(cuò)所需具備的心智能力。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之所以不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是因?yàn)樗麄儾痪邆溥^錯(cuò)能力,其致人損害時(shí)的主觀狀態(tài)不能被認(rèn)定為過錯(cuò),按照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民事責(zé)任當(dāng)然不能成立。
四、《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評(píng)析:缺陷及其完善
基于以上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能力適用范圍及其本質(zhì)的考察結(jié)論,可以對(duì)我國現(xiàn)行法中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予以檢討和重塑。在這個(gè)問題上,《侵權(quán)責(zé)任法》基本上沿襲了《民法通則》第133條的規(guī)范模式。鑒于《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規(guī)定存在明顯的缺陷,筆者建議在以下幾個(gè)方面加以完善。
(一)只應(yīng)將被監(jiān)護(hù)人的財(cái)產(chǎn)能力作為其承擔(dān)公平責(zé)任的基礎(chǔ)
從《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2款來看,有財(cái)產(chǎn)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需要支出賠償費(fèi)用,實(shí)際上等于說需要承擔(dān)損害賠償責(zé)任,而監(jiān)護(hù)人只承擔(dān)補(bǔ)充責(zé)任。行為人是否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取決于其是否擁有財(cái)產(chǎn),不論其是否具有行為的識(shí)別能力。哪怕是6歲的兒童,如果有財(cái)產(chǎn),也需要對(duì)其行為承擔(dān)責(zé)任;相反,一個(gè)17歲的青年,如果沒有財(cái)產(chǎn),不需要對(duì)其致害行為負(fù)責(zé)。識(shí)別能力強(qiáng)的青年反而比識(shí)別能力差的兒童更受法律的優(yōu)待,這種做法在倫理上難以正當(dāng)化。
對(duì)于侵權(quán)責(zé)任的承擔(dān),我國立法者實(shí)際上在過錯(cuò)能力意義上的責(zé)任能力之外又確立了另一個(gè)責(zé)任前提,即財(cái)產(chǎn)能力。只要致害人具備過錯(cuò)能力和財(cái)產(chǎn)能力這兩個(gè)責(zé)任前提中的一個(gè),他就需要承擔(dān)責(zé)任。我們可以將這種規(guī)范模式稱為“雙軌式的侵權(quán)責(zé)任法律前提”。其立法目的主要是:充分救濟(jì)受害人,防止在監(jiān)護(hù)人財(cái)產(chǎn)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受害人得不到賠償;[37]減輕監(jiān)護(hù)人的負(fù)擔(dān),避免出現(xiàn)沒有人愿意擔(dān)任監(jiān)護(hù)人的狀況。[38]這種做法盡管確實(shí)有這兩個(gè)方面的積極意義,但這種規(guī)范模式也存在明顯弊端:(1)在法價(jià)值層面上缺乏充分的正當(dāng)性。一般認(rèn)為,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倫理根基在于自由意志論。與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相配套的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也是以該理論為倫理根基的,只有具備自由選擇能力的人才具有民事責(zé)任能力。古典自然法學(xué)家普芬道夫認(rèn)為,人的任何自愿行為的原動(dòng)力都在于其理智,如果某人不具備清楚地辨別是非的能力,那么他所實(shí)施的錯(cuò)誤行為就不能作為一種過錯(cuò)而歸責(zé)于他,否則就是嚴(yán)重的不公正;不過,任何一個(gè)沒有精神障礙的成年人都具備足夠的理智確保自己的行為符合自然法的準(zhǔn)則,所以其行為都是可歸責(zé)的。[39]《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2款單純以財(cái)產(chǎn)狀況這種外在因素決定未成年人和精神障礙者是否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導(dǎo)致侵權(quán)責(zé)任完全喪失了倫理性,背離了侵權(quán)責(zé)任制度和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的本質(zhì)。(2)容易導(dǎo)致監(jiān)護(hù)人玩忽職守。既然可以從被監(jiān)護(hù)人財(cái)產(chǎn)中支出賠償費(fèi)用,那么監(jiān)護(hù)人也就不必那么認(rèn)真履行監(jiān)護(hù)職責(zé)了,尤其是在監(jiān)護(hù)人并非被監(jiān)護(hù)人父母的情況下這種弊端更加明顯。(3)不利于維護(hù)被監(jiān)護(hù)人的利益。讓一個(gè)年幼無知或精神錯(cuò)亂缺乏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以其財(cái)產(chǎn)賠償他人損失而監(jiān)護(hù)人即使嚴(yán)重失職也不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不但顯然有失公平而且還可能導(dǎo)致被監(jiān)護(hù)人喪失生活或未來發(fā)展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
筆者認(rèn)為,《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2款不符合侵權(quán)責(zé)任的基本原理,無論在倫理上還是在比較法上都缺乏正當(dāng)依據(jù),應(yīng)該依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基本原理對(duì)該款予以修改。如前所述,民事責(zé)任能力在本質(zhì)上是過錯(cuò)能力,因此被監(jiān)護(hù)人是否承擔(dān)一般侵權(quán)責(zé)任取決于其是否具備過錯(cuò)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財(cái)產(chǎn)能力。被監(jiān)護(hù)人的財(cái)產(chǎn)能力充其量只能作為其承擔(dān)公平責(zé)任的基礎(chǔ)。從比較法上看,在規(guī)定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同時(shí),很多國家的民法均規(guī)定了無責(zé)任能力人的補(bǔ)充性公平責(zé)任,即在受害人不能從負(fù)有監(jiān)督義務(wù)的人如監(jiān)護(hù)人那里獲得損害賠償?shù)那闆r下,為公平起見,可以在不剝奪無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人的生計(jì)且不影響其履行法定扶養(yǎng)義務(wù)的前提下判令其承擔(dān)賠償義務(wù),如《德國民法典》第829條、《奧地利民法典》第1310條、《俄羅斯聯(lián)邦民法典》第1076條第3款、《意大利民法典》第2047條2款、《葡萄牙民法典》第489條、《希臘民法典》第918條。而且,《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24條針對(duì)一般侵權(quán)行為規(guī)定了普適性的公平責(zé)任,其適用范圍也應(yīng)該包括被監(jiān)護(hù)人承擔(dān)公平責(zé)任。總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2款規(guī)定是多余的。在立法論層面上,該款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刪除。在解釋論層面上,應(yīng)當(dāng)對(duì)該款予以目的性限縮,將其解釋為只有在受害人無法從監(jiān)護(hù)人那里獲得賠償?shù)那闆r下有財(cái)產(chǎn)的被監(jiān)護(hù)人才承擔(dān)賠償責(zé)任,而且只承擔(dān)公平責(zé)任。
(二)應(yīng)該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予以更細(xì)致的劃分
從《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1款的規(guī)定來看,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都不具備民事責(zé)任能力,其致害行為由監(jiān)護(hù)人負(fù)責(zé),只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才具備民事責(zé)任能力。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標(biāo)準(zhǔn)顯然高于法律行為能力,也高于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刑事責(zé)任能力年齡標(biāo)準(zhǔn)。與民事責(zé)任相比,刑事責(zé)任對(duì)行為人的不利影響更大。易言之,民事責(zé)任較輕,刑事責(zé)任較重。與此相應(yīng),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年齡標(biāo)準(zhǔn)本應(yīng)低于刑事責(zé)任能力的年齡標(biāo)準(zhǔn),但《侵權(quán)責(zé)任法》卻反其道而行之。這種立法例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獨(dú)一無二的。造成這一結(jié)果的原因在于我國民法的立法者忽略了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倫理價(jià)值,沒有充分意識(shí)到民事責(zé)任能力在本質(zhì)上是過錯(cuò)能力。只有在理論上強(qiáng)調(diào)民事責(zé)任能力的本質(zhì)是過錯(cuò)能力,才可能以年齡和識(shí)別能力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被監(jiān)護(hù)人的責(zé)任能力進(jìn)行細(xì)分,因?yàn)橐欢ǖ哪挲g和識(shí)別能力是過錯(cuò)的基礎(chǔ)。至于監(jiān)護(hù)人是否也應(yīng)該對(duì)此承擔(dān)責(zé)任,那是另一個(gè)問題,在此不再展開了。
從比較法上看,大陸法系國家或地區(qū)民法關(guān)于未成年人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判定存在四種規(guī)范模式。一是出生主義,以法國民法為代表。在當(dāng)代法國民法中,任何人自其出生之后都具有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40]二是抽象標(biāo)準(zhǔn)主義,具有代表性的是《荷蘭民法典》。《荷蘭民法典》是以14歲這一抽象的年齡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行為人是否具有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的。三是具體認(rèn)定主義。責(zé)任能力的有無取決于識(shí)別能力之有無,而后者只能具體判斷,沒有事先確定的統(tǒng)一標(biāo)準(zhǔn),如年齡。《日本民法典》第712條以及我國臺(tái)灣地區(qū)所謂“民法”第187條第1款均采用該規(guī)范模式。四是抽象標(biāo)準(zhǔn)和具體認(rèn)定相結(jié)合主義。《德國民法典》第828條規(guī)定的侵權(quán)責(zé)任能力兼采抽象的年齡標(biāo)準(zhǔn)和具體的識(shí)別能力標(biāo)準(zhǔn)。前者適用于7周歲以下的兒童以及交通事故中的10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不具備責(zé)任能力;后者適用于其他未成年人,需要考察其在行為時(shí)是否具備對(duì)于認(rèn)知責(zé)任所必需的理解力。
筆者認(rèn)為,作為過錯(cuò)能力,民事責(zé)任能力是以致害人的心智能力作為基礎(chǔ)的。因?yàn)檫^錯(cuò)歸根結(jié)底是一種應(yīng)受責(zé)難的心理狀態(tài),即致害人本應(yīng)選擇對(duì)他人無害的行為但卻做了相反的選擇。這種選擇要求致害人具備識(shí)別、理解能力。既然如此,那么判定致害人是否具備民事責(zé)任能力就應(yīng)該以其心智能力的狀況為準(zhǔn)。對(duì)此,最理想的做法是具體認(rèn)定主義,即在個(gè)案中對(duì)致害人是否具備識(shí)別、理解其行為所需要的心智能力進(jìn)行具體認(rèn)定,據(jù)此判定其是否需要承擔(dān)過錯(cuò)責(zé)任。不過,這種做法成本太高,而且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容易導(dǎo)致法官濫用自由裁量權(quán)。在法官的專業(yè)水準(zhǔn)和道德素養(yǎng)不夠高的情況下,采用具體認(rèn)定主義風(fēng)險(xiǎn)太大。比較現(xiàn)實(shí)的做法是對(duì)未成年人采用抽象標(biāo)準(zhǔn)和具體認(rèn)定相結(jié)合主義,即規(guī)定一定年齡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具備民事責(zé)任能力,對(duì)該年齡以上的未成年人則在個(gè)案中具體認(rèn)定是否具備與致害行為相應(yīng)的民事責(zé)任能力。這樣可以兼顧法的安定性和個(gè)案的妥當(dāng)性。對(duì)精神障礙者只能采用具體認(rèn)定主義,在個(gè)案中確定其是否具有民事責(zé)任能力。
至于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在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上應(yīng)該是什么關(guān)系,筆者認(rèn)為,從理論上說,行為人對(duì)其致害行為違法性的認(rèn)識(shí)比對(duì)其法律行為效果的認(rèn)識(shí)通常要容易一些。一個(gè)12歲的未成年人通常都知道打傷別人是不對(duì)的,但卻未必知道出租一套房屋的法律意義和風(fēng)險(xiǎn)。不過兩者之間的差距并不是那么明顯以至于需要對(duì)其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予以嚴(yán)格區(qū)分。至少在抽象標(biāo)準(zhǔn)上對(duì)民事責(zé)任能力與法律行為能力不必區(qū)分。也就是說,無法律行為能力人與無民事責(zé)任能力人的年齡標(biāo)準(zhǔn)應(yīng)該是一樣的,否則將導(dǎo)致民法上對(duì)人的年齡劃分過于繁雜,有損民法的簡明性。在立法論層面上,應(yīng)該比照《民法通則》第12條的規(guī)定將未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規(guī)定為無民事責(zé)任能力人,將10周歲以上的未成年人規(guī)定為限制民事責(zé)任能力人。對(duì)限制民事責(zé)任能力的具體認(rèn)定,法官在標(biāo)準(zhǔn)的掌握上可稍低于限制法律行為能力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換言之,對(duì)過錯(cuò)致害行為的成立,不需要具備民事法律行為所要求的那種程度的識(shí)別和理解能力。
(三)應(yīng)該限定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
《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未明確規(guī)定民事責(zé)任能力的適用范圍,在實(shí)踐中容易使人誤以為其不僅適用于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也適用于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特殊侵權(quán)責(zé)任,但這顯然不是正確的理解。作為過錯(cuò)能力,民事責(zé)任能力在侵權(quán)法領(lǐng)域僅適用于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不具備過錯(cuò)能力的被監(jiān)護(hù)人需要承擔(dān)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例外的是,對(duì)《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72條規(guī)定的高度危險(xiǎn)物致害責(zé)任以及第78條規(guī)定的飼養(yǎng)動(dòng)物致害責(zé)任,如果被監(jiān)護(hù)人欠缺足夠的識(shí)別能力,不能成為占有人、飼養(yǎng)人或管理人,則不必承擔(dān)侵權(quán)責(zé)任,但這些危險(xiǎn)物或動(dòng)物系用于營業(yè)的除外。筆者認(rèn)為,在立法論層面上,應(yīng)該在《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中增加一款,規(guī)定前款關(guān)于民事責(zé)任能力(過錯(cuò)能力)的規(guī)定不適用于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同時(shí)在第72條和第78條再作特殊規(guī)定。在解釋論層面上,可以考慮對(duì)《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32條第2款作目的性限縮,將其中的“財(cái)產(chǎn)”解釋為用于營業(yè)的財(cái)產(chǎn),將“損害”解釋為因營業(yè)性活動(dòng)而導(dǎo)致的損害。這樣,該款的含義就被限縮為:(1)就實(shí)行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侵權(quán)責(zé)任而言,在受害人無法從監(jiān)護(hù)人那里獲得賠償?shù)那闆r下,有財(cái)產(chǎn)的被監(jiān)護(hù)人承擔(dān)公平責(zé)任;(2)就實(shí)行無過錯(cuò)責(zé)任原則的因營業(yè)性活動(dòng)而發(fā)生的侵權(quán)責(zé)任而言,被監(jiān)護(hù)人應(yīng)該以其財(cái)產(chǎn)承擔(dān)損害賠償責(zé)任。
注釋:
[1]參見龍衛(wèi)球:《民法總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33頁;劉保玉、秦偉:《論自然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法學(xué)研究》2001年第2期。
[2][3]參見余延滿、橋:《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的若干問題———與劉保玉、秦偉同志商榷》,《法學(xué)研究》2001年第6期。
[4]有學(xué)者認(rèn)為此種情形中,未成年人作為合同主體在履行中如有過錯(cuò)和瑕疵則直接據(jù)此認(rèn)定未成年人成立違約責(zé)任。參見姜戰(zhàn)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責(zé)任承擔(dān)研究》,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頁。這種觀點(diǎn)值得商榷。由法定人代為訂立合同時(shí),未成年人通常不會(huì)自己履行債務(wù),即便自己履行了,因其欠缺識(shí)別能力也不構(gòu)成過錯(cuò)。
[5]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頁。
[6]Vgl.BSK ORI-Wiegand/in,Art.101N8.
[7]參見[日]我妻榮:《新訂債權(quán)總論》,王燚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頁。
[8]參見李慶海:《論民事行為能力與民事責(zé)任能力》,《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劉保玉、秦偉:《論自然人的民事責(zé)任能力》,《法學(xué)研究》2001年第2期;姜戰(zhàn)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責(zé)任承擔(dān)研究》,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頁。
[9]Vgl.Fikentscher/Heinemann,Schuldrecht,10.Aufl.,De Gruyter Rechtswissenschaften Verlags-GmbH,Berlin,2006,S.691-693.
[10]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2):不當(dāng)?shù)美罚袊ù髮W(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9頁。
[11]參見王澤鑒:《民法學(xué)說與判例研究》第5冊(cè),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第127-128頁;[德]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5頁。
[12]參見[德]梅迪庫斯:《德國債法分論》,杜景林、盧諶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7—558頁。
[13]參見王澤鑒:《民法學(xué)說與判例研究》第5冊(cè),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第127-129頁。
[14][15]Vgl.Günter Christian Schwarz/Manfred Wandt,Gesetzliche Schuldverhaltnisse,3.Aufl.,Verlag Franz Vahlen,München,2009,S.74,S.64.
[16]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頁;王澤鑒:《民法學(xué)說與判例研究》第5冊(cè),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第124頁。
[17]Vgl.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33.Aufl.,Verlag C.H.Beck,München,2008,S.426.
[18]參見王澤鑒:《債法原理(1):基本理論·債之發(fā)生》,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頁。對(duì)此有學(xué)者持相反觀點(diǎn),認(rèn)為在不當(dāng)無因管理的情形中,管理人的責(zé)任并非侵權(quán)責(zé)任,而是債務(wù)不履行責(zé)任。參見姜戰(zhàn)軍:《未成年人致人損害責(zé)任承擔(dān)研究》,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頁。
[19][20]參見邱聰智:《從侵權(quán)行為歸責(zé)原理之變動(dòng)論危險(xiǎn)責(zé)任之構(gòu)成》,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6頁,第263-266頁。
[21]從語義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quán)責(zé)任法》第89條規(guī)定的“堆放”、“傾倒”都屬于有過錯(cuò)的行為,而“遺撒”則可能是有過錯(cuò)行為,也可能是無過錯(cuò)的行為,如某人運(yùn)輸之物品意外遺落于公路上,造成事故致他人損害。
[22]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第1款第2項(xiàng)的規(guī)定,機(jī)動(dòng)車與非機(jī)動(dòng)車駕駛?cè)恕⑿腥酥g發(fā)生交通事故,機(jī)動(dòng)車一方?jīng)]有過錯(cuò)的,承擔(dān)不超過10%的賠償責(zé)任。
[23]參見[德]鮑爾、施蒂爾納:《德國物權(quán)法》(上),張雙根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頁;謝在全:《民法物權(quán)論》,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931頁;[日]近江幸治:《民法講義II:物權(quán)法》,王茵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頁。
[24]Vgl.Deutsch/Ahrens,Deliktsrecht,Carl Heymanns Verlag,Kaln,2009,S.162;Esser/Weyers,Schuldrecht,Bd.II,BesondererTeil,C.F.Müller JuristischerVerlag,Heidelberg,1984,S.544.
[25]Vgl.PWW/Schaub,§827Rn.2.
[26]Vgl.BSK ZGB I-Bigler-Eggenberger/in,Art.18N20;BSK OR I-Schnyder/in,Art.58N3.
[27]See The Civil Code of the Netherlands,translated by Hans Warendorf,Richard Thomas &Ian Curry-Sumner,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9,p.685.
[28][40]參見[德]克雷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quán)行為法》(上),張新寶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第97-100頁。
[29][30]參見[意]彼德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fēng)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43-44頁,第44頁。
[31]參見D.4,3,13,1;D.47,2,23,2;D.44,4,4,26;D.50,17,111pr.;[古羅馬]蓋尤斯:《法學(xué)階梯》,黃風(fēng)譯,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276頁。
[32]Vgl.C.F.Koch,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Thl.1,Bd.1,4.Aufl.,Verlag von J.Guttentag,1862,S.374.;Moriz von Stubenrauch,Das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vom 1.Juni 1811,Bd.3,Verlag von Friedrich Manz,Wien,1858,S.525-527.
[33]Vgl.Hepp,Die Zurechnung auf dem Gebiete des Civilrechts,C.F.Osiander,Tübingen,1838,S.123.
[34]See Christian Thomasius,Larva legis Aquiliae detracta actioni de damno dato receptae in foris germanorum,translated by MargaretHewett,Hart Publishing,Oxfoerd and Portland,2000,pp.5-46.
[35]Vgl.MünchKomm/Wagner,§827Rn.1.
[36]Vgl.Esser/Schmidt,Schuldrecht,Bd.I,Allgemeiner Teil,6.Aufl.,C.F.Müller Juristischer Verlag,Heidelberg,1984,S.370;Brox/Walker,Besonderes Schuldrecht,33.Aufl.,Verlag C.H.Beck,München,2008,S.492.
[37]參見王利明:《自然人民事責(zé)任能力制度探討》,《法學(xué)家》2011年第2期。
篇5
【關(guān)鍵詞】刑法解釋 常識(shí)化 專業(yè)解釋 裁判規(guī)范
一、法律解釋常識(shí)化的觀念
翻閱刑法學(xué)方面的書籍和文章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gè)問題,刑法學(xué)理與司法實(shí)踐兩者之間,在認(rèn)知范圍、思維方式和理解程度等方面的差別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無論是研究領(lǐng)域的專著、教科書,還是實(shí)踐領(lǐng)域中的司法解釋,基本上都是在現(xiàn)象的范圍內(nèi)討論刑法條文的內(nèi)容、法律適用的條件,根據(jù)具體案件的個(gè)別特征,經(jīng)驗(yàn)性地闡述和說明刑法規(guī)范的含義幾乎是一種普遍的模式。這種以常識(shí)知識(shí)為基礎(chǔ)解讀刑法條文的普遍現(xiàn)象,似乎使人感覺到刑法解釋只關(guān)心如何才能符合“人情常理”,卻不在意解釋的根據(jù)是否建立在法律科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或許以為,經(jīng)驗(yàn)常識(shí)與刑法理論之間原本就不像其他科學(xué)那樣有著很大的差別。難怪刑法學(xué)經(jīng)常會(huì)被其他學(xué)科稱為典型的“實(shí)踐法學(xué)”,是一種“缺乏理論思辨根基”的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體系。
人們習(xí)慣于在常識(shí)的層面上分析、討論和評(píng)價(jià)刑法條文的規(guī)定和刑法學(xué)的理論問題,原因是由于刑法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是對(duì)公眾的社會(huì)舉止提出的強(qiáng)制性要求,所以,只要了解漢語詞句基本的使用方法和表達(dá)習(xí)慣,并具有一定的日常生活經(jīng)驗(yàn),就應(yīng)當(dāng)能夠讀懂法律條文,并且不辜負(fù)法律的期待實(shí)施法律所允許的行為。在人們的觀念中,對(duì)刑法規(guī)范理解的正確與否,更多情況下是以符合社會(huì)一般公眾的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為標(biāo)準(zhǔn)的,當(dāng)然,人們對(duì)法律規(guī)定的理解也會(huì)發(fā)生分歧,在這種情況下,相信司法機(jī)關(guān)或權(quán)威人士做出的解釋是無可置疑的,盡管這些解釋也是經(jīng)驗(yàn)的、常識(shí)性的,但卻不應(yīng)當(dāng)是脫離法律的客觀性、科學(xué)性而隨意做出的。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能夠得到普遍地遵守,而社會(huì)公眾對(duì)法律規(guī)范的理解、接受,對(duì)于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和維護(hù)生活的穩(wěn)定、有序是至關(guān)重要的。正如一些學(xué)者所言:只要能夠得到公眾觀念認(rèn)同的刑法解釋就是正確有效和無可懷疑的。[1]
條文解釋的常識(shí)化和學(xué)理研究的經(jīng)驗(yàn)化,雖然是我國刑法學(xué)研究和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gè)顯著特點(diǎn),但是我國刑法學(xué)卻沒有對(duì)“常識(shí)化解釋”這一問題進(jìn)行深入的討論和研究,所以,人們對(duì)這一概念可能會(huì)感到很陌生。其實(shí),常識(shí)觀念與法律觀念之間的沖突一直伴隨刑法學(xué)研究和發(fā)展的各個(gè)階段。所謂“常識(shí)化解釋”在刑法學(xué)中大致有兩種表述形式:一種被稱之為“刑法解釋上的公眾認(rèn)同”,如周光權(quán)博士提到的,以“市民規(guī)范性意識(shí)”、“市民感覺”、“刑法的國民認(rèn)同感”、“國民的經(jīng)驗(yàn)、情感”、“一般人的常識(shí)”、“公眾的一般感覺”為標(biāo)準(zhǔn)對(duì)刑法規(guī)范作出的解釋。[2]這種刑法的常識(shí)化解釋,就是從法律遵守的意義上以社會(huì)公眾根據(jù)生活經(jīng)驗(yàn)?zāi)軌蛑苯永斫狻⒄J(rèn)同和接受為標(biāo)準(zhǔn)來確定刑法規(guī)定的內(nèi)容和含義的,對(duì)法律規(guī)范理解的正確與否,取決于一般國民的判斷能力和水平,而違背社會(huì)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即使是權(quán)威性的解釋也毫無例外地被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是所謂的“社會(huì)相當(dāng)性”。如日本刑法學(xué)教科書中提到的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社會(huì)文化規(guī)范。日本學(xué)者大谷實(shí)教授認(rèn)為,所謂的社會(huì)秩序,是以各個(gè)生活領(lǐng)域中所形成的一般妥當(dāng)?shù)纳鐣?huì)倫理規(guī)范為基礎(chǔ)而得以維持的,而刑法所追求的就是以這種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為基礎(chǔ)的現(xiàn)實(shí)存在的社會(huì)秩序的維持和發(fā)展。[3]從這一意義上講,刑法乃至一切法律的制定、適用和遵守,都是在常識(shí)觀念指導(dǎo)下的經(jīng)驗(yàn)性過程。按照日本學(xué)者的觀點(diǎn),刑法條文規(guī)定的構(gòu)成要件,是按照一般社會(huì)觀念將應(yīng)當(dāng)處罰的行為進(jìn)行類型化的東西,因此按照一般社會(huì)觀念認(rèn)定案件事實(shí)與構(gòu)成要件的符合性,并追究其責(zé)任是妥當(dāng)?shù)摹4]在這一意義上,常識(shí)化解釋是從法律適用的立場(chǎng)強(qiáng)調(diào)刑法解釋要以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為基礎(chǔ),因?yàn)樾谭ㄋS持和發(fā)展的現(xiàn)實(shí)存在的社會(huì)秩序,是以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為基礎(chǔ)的。所謂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按照大谷實(shí)教授的理解,是以人們的智慧為基礎(chǔ)作為社會(huì)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歷史形成的。行為只要不與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相抵觸,就不會(huì)侵害社會(huì)秩序,也不會(huì)喚起社會(huì)公眾懲治處罰的情感需求。[5]因此,不符合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的刑法解釋也不能被認(rèn)為是正確的。
根據(jù)上述兩種表述形式,我們可以這樣來定義常識(shí)化解釋:所謂刑法的常識(shí)化解釋,實(shí)際上是指運(yùn)用一般人具有的常識(shí)經(jīng)驗(yàn)、倫理觀念和通俗的生活語言,對(duì)刑法規(guī)范的內(nèi)容和應(yīng)用范圍所作出的感性描述和直觀說明;是為了使人們能夠在專業(yè)性知識(shí)之外理解、接受、遵守和應(yīng)用刑罰法規(guī)的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作為關(guān)于刑罰法規(guī)知識(shí)介紹和說明的方法,常識(shí)化解釋的一個(gè)最突出特點(diǎn)就是通俗易懂、符合生活常識(shí),沒有概念的抽象性,不存在專業(yè)術(shù)語的障礙,對(duì)法律條文的分析、論證、推斷和結(jié)論,都是在常識(shí)觀念的語境中進(jìn)行的。在筆者看來,常識(shí)化解釋至少有以下四個(gè)特點(diǎn):
(1)解釋者以生活常識(shí)為基礎(chǔ),從經(jīng)驗(yàn)的層面勾畫、描述和構(gòu)建刑法規(guī)范的可感性模型。例如,刑法第三條關(guān)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規(guī)定,大多數(shù)教科書都解釋為:“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聆聽者不必經(jīng)過專門的法科學(xué)習(xí),也無需了解法學(xué)原理中的專門知識(shí),只要具有一定的社會(huì)常識(shí)和生活經(jīng)驗(yàn),就可以通過這種解釋在頭腦中形成關(guān)于罪刑法定原則的表象。
(2)運(yùn)用通俗的語言,將條文中僵硬的文字轉(zhuǎn)化成日常生活中多彩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將單調(diào)或者陌生的法律概念演繹成具體、生動(dòng)的畫面。日常生活語言的普及性,使人們對(duì)所有的法律問題都可以進(jìn)行交流、討論,不必?fù)?dān)心專業(yè)術(shù)語的障礙、法學(xué)基礎(chǔ)理論的晦澀,以及法律思維的嚴(yán)謹(jǐn)會(huì)對(duì)他們理解法律規(guī)范帶來影響。例如,將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解釋為:具有社會(huì)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和應(yīng)受刑罰處罰性的行為,其中社會(huì)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zhì)特征。概念是對(duì)事物本質(zhì)特征的闡述,所以通常是抽象的、晦澀難懂的,以通俗的語言化解概念的抽象性是常識(shí)化解釋的重要特征。
我們知道,一般公民與司法機(jī)關(guān)對(duì)刑法規(guī)范理解的同一性是建立在日常用語基礎(chǔ)之上的,而漢語的特點(diǎn)和表意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又是耳熟能詳、眾所周知的。因此在常識(shí)化解釋的范圍內(nèi),律師、法官、學(xué)者與社會(huì)公眾在條文詞句的理解上應(yīng)當(dāng)是無差別的、平等的,在現(xiàn)代漢語語言表述規(guī)則的范圍內(nèi),很難形成有“高人一等”或“勝人一籌”的“學(xué)術(shù)權(quán)威”。[6]作為刑罰法規(guī)的刑法,既約束一般公民的社會(huì)行為,也規(guī)范司法機(jī)關(guān)的刑事裁量活動(dòng),限制學(xué)者們對(duì)規(guī)范內(nèi)容以及適用條件的認(rèn)識(shí)。“常識(shí)是人們?cè)谌粘I钪械墓餐?jīng)驗(yàn),它使人們的行為方式得到最直接的相互協(xié)調(diào)”。[7]正是在常識(shí)觀念的范圍內(nèi),刑法解釋的權(quán)威性才不被少數(shù)的法學(xué)家、法官所壟斷,人們對(duì)法律認(rèn)識(shí)的統(tǒng)一性才能夠得以實(shí)現(xiàn)。當(dāng)人們對(duì)法律條文的理解產(chǎn)生爭論時(shí),即使擁有最終解釋權(quán)的國家審判機(jī)關(guān)或者法官,也必須對(duì)自己的決定作出符合常識(shí)觀念的解釋。
(3)感性直觀構(gòu)成要件與行為事實(shí)的符合性。常識(shí)化解釋可以將案件個(gè)別事實(shí)與法律條文的一般性規(guī)定加以對(duì)照、比較,使人們根據(jù)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yàn),理解或認(rèn)同該行為是否為法律所禁止,以及依法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多重的刑事責(zé)任。在法律適用過程中,刑法解釋的主要任務(wù)就是在闡述法律條文基本含義的基礎(chǔ)上,說明案件事實(shí)是否屬于某一法律規(guī)范調(diào)整的范圍之內(nèi)。如果說刑罰法規(guī)是司法機(jī)關(guān)定罪量刑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那么生活經(jīng)驗(yàn)和常識(shí)知識(shí)就是衡量行為事實(shí)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基本尺度。脫離感性經(jīng)驗(yàn)或者不符合常識(shí)的刑法解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對(duì)廣大社會(huì)公眾而言,法律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取決于它所作出的規(guī)定能否在經(jīng)驗(yàn)常識(shí)的層面上得到普遍的認(rèn)同、信服,而不僅在于它的強(qiáng)制性。因此,有助于法律公正與效率的有機(jī)統(tǒng)一,是常識(shí)性解釋的又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
(4)是一種現(xiàn)象層面的解釋,通常不涉及刑罰法規(guī)的本質(zhì)、規(guī)律和價(jià)值等方面內(nèi)容。犯罪構(gòu)成是違法性和責(zé)任的表象,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現(xiàn)象是個(gè)別的、感性的、易變的和多樣化的,對(duì)同一刑法規(guī)范的感性認(rèn)識(shí),可能會(huì)因角度的不同而得出諸多不同的結(jié)論。而違法性與責(zé)任之間的關(guān)系則是一般的、本質(zhì)的、穩(wěn)定的。所以,當(dāng)現(xiàn)象層面的解釋發(fā)生分歧和爭論的場(chǎng)合,如果不通過科學(xué)的解釋,往往是無法判斷其結(jié)論的正確性與客觀性的。在司法實(shí)踐中,刑法的權(quán)威解釋者是審判機(jī)關(guān)(在更多場(chǎng)合下是法官),它有權(quán)對(duì)爭執(zhí)不休的各種意見作出最后的選擇。這樣一來,“解釋效力”則具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性,而解釋的科學(xué)性、客觀性只有在被效力解釋接受的場(chǎng)合才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綜上所述,刑法的常識(shí)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的方法其作用是重要的、可替代的。這種方法在刑法適用和普及法律的宣傳教育活動(dòng)中,既方便國民對(duì)法律的理解和遵守,也便于社會(huì)公眾對(duì)司法審判以及其他刑事訴訟活動(dòng)的監(jiān)督和支持,從這一點(diǎn)上,常識(shí)化解釋是合理的、正確的和具有積極意義的。然而,刑法學(xué)是一門法律科學(xué),所謂科學(xué)是對(duì)事物的本質(zhì)以及發(fā)展規(guī)律的探索和認(rèn)識(shí),是“具有嚴(yán)謹(jǐn)?shù)倪壿嬓院拖到y(tǒng)性,普遍的解釋性和規(guī)范性的概念發(fā)展體系”,對(duì)法律條文含義的經(jīng)驗(yàn)性解說應(yīng)當(dāng)以刑法科學(xué)的普遍性、客觀性為前提,這是科學(xué)研究及發(fā)展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二、法律科學(xué)中常識(shí)化解釋的悖論
在刑法學(xué)的學(xué)習(xí)和研究中,經(jīng)常會(huì)遇到這樣一些難以理解的現(xiàn)象。有人初學(xué)法律,甚至連法理學(xué)的基本概念還沒有弄清楚,就可以高談闊論“刑法理論”中某一主要觀點(diǎn),指出法律中存在的各種漏洞和不足;而有人從事刑法教學(xué)研究多年,對(duì)刑法學(xué)的理解仍然停留在感性經(jīng)驗(yàn)和常識(shí)知識(shí)的水平。人們不禁要問,刑法學(xué)究竟是不是科學(xu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來要回答的就是:什么是科學(xué)?在科學(xué)領(lǐng)域中生活常識(shí)與專業(yè)知識(shí)是不是應(yīng)當(dāng)有所區(qū)別呢?什么是理論?概念思維與經(jīng)驗(yàn)知覺在科學(xué)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應(yīng)當(dāng)有所不同呢?理論研究與司法實(shí)踐的結(jié)合是否意味著兩者可以混淆或者互相代替呢?筆者不想在該文中對(duì)諸如科學(xué)、理論、概念思維、專業(yè)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感知等概念作詳細(xì)地分析論證,但至少有一點(diǎn)應(yīng)當(dāng)肯定,那就是對(duì)這些概念含義的理解和解釋不是隨心所欲、任意性的,而應(yīng)當(dāng)是規(guī)范的、確定的,與之相關(guān)的基礎(chǔ)性知識(shí)應(yīng)當(dāng)是統(tǒng)一的。并且這些內(nèi)容都是作為一門科學(xué)知識(shí)體系所不可或缺的。
首先,我們要面對(duì)的是刑法專業(yè)知識(shí)與生活常識(shí)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我們知道,常識(shí)經(jīng)驗(yàn)與專業(yè)知識(shí)是有差別的。專業(yè)知識(shí)通常是指某一領(lǐng)域中所特有的技術(shù)、技能,以及相關(guān)的操作程序和行業(yè)術(shù)語等方面的系統(tǒng)性學(xué)問,是從事某種“職業(yè)”、“業(yè)務(wù)”所必須運(yùn)用,的專門化知識(shí)。作為專業(yè)的法律工作者,必須受過專門的培訓(xùn)、考核,包括法學(xué)基礎(chǔ)知識(shí)的學(xué)習(xí)、職業(yè)技能的培訓(xùn)和法律思維方式等方面的訓(xùn)練,因?yàn)橹挥型ㄟ^專門學(xué)習(xí)并考試合格的人員,才有可能正確地把握和應(yīng)用這些知識(shí)、技能,才能夠勝任具有嚴(yán)格職業(yè)或職務(wù)要求的法律工作。對(duì)于一般公民來說,盡管法律作為行為規(guī)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guān),與他們的自身安全密切相連,所以他們應(yīng)當(dāng)對(duì)法律有所了解、關(guān)心,必須知道遵守法律是每一個(gè)社會(huì)成員的義務(wù)。可是他們大都并沒有經(jīng)過專門的學(xué)習(xí)和訓(xùn)練,對(duì)法律規(guī)范的理解局限于常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的范圍,法律對(duì)他們的要求也只限于能夠?qū)`反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的行為作出一般性的判斷。當(dāng)然,隨著社會(huì)成員文化素質(zhì)的提高和法律意識(shí)的增強(qiáng),法律對(duì)他們的要求會(huì)更加嚴(yán)格,但要求再高,也很難達(dá)到法律專業(yè)人士的水準(zhǔn)。對(duì)于法律實(shí)務(wù)工作者而言,刑法是一種職業(yè)上的操作規(guī)程和制度,法律的適用有著特殊的專業(yè)要求和嚴(yán)格的技術(shù)規(guī)范,并非只是單純地應(yīng)合、隨附社會(huì)公眾的法制觀念和法律心理,對(duì)發(fā)生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刑事案件,要運(yùn)用法律專業(yè)知識(shí)做出分析判斷,要遵循司法職業(yè)技術(shù)的基本要求進(jìn)行裁量,刑事法律作為司法機(jī)關(guān)和法律職業(yè)群體職務(wù)行為的操作規(guī)范,必須嚴(yán)格地遵守,法律實(shí)務(wù)工作者在履行職責(zé)的操作中違反規(guī)程,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瀆職行為,甚至可能構(gòu)成犯罪。我國在現(xiàn)階段對(duì)職業(yè)法律工作者提出了更加嚴(yán)格的要求,恰恰說明了法律工作必須具備較強(qiáng)的專業(yè)性,而不能始終停留在常識(shí)經(jīng)驗(yàn)的水平。
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是零散的、模糊的、個(gè)別的和自發(fā)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職業(yè)技能則是系統(tǒng)的、確定的、普遍的和自覺的。專業(yè)人員對(duì)于案件事實(shí)的認(rèn)識(shí),通常是從法律規(guī)范的角度展開的。例如,造成他人傷害、死亡的行為,無論是從常識(shí)的角度還是站在專業(yè)的立場(chǎng)上,一般被認(rèn)為是構(gòu)成犯罪的。但是,與一般公民的常識(shí)觀念不同,專業(yè)人員能夠較為準(zhǔn)確地說明,在哪些情況下行為雖然導(dǎo)致他人重傷或死亡,但行為人卻不構(gòu)成犯罪;在哪些情況下行為造成同樣的危害后果會(huì)減免或者加重行為人的責(zé)任;能夠判斷該行為在何種情況下符合傷害罪或殺人罪的構(gòu)成要件、在何種情況下應(yīng)當(dāng)認(rèn)定為其他的罪名;根據(jù)專業(yè)知識(shí)區(qū)分何種情況下是一罪、何種情況下是數(shù)罪等等,這些通常是一般公民所做不到的。也就是說,在犯罪性質(zhì)認(rèn)定和刑事責(zé)任判斷等重要問題上,僅依靠公眾的常識(shí)性觀念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我們不排除缺乏專業(yè)知識(shí)的人也能講出符合“人情事故”的道理來說明該行為事實(shí)違法、犯罪的性質(zhì),甚至十分的生動(dòng)感人,而且誰也沒有權(quán)利禁止他們這樣理解和解釋法律,但在涉及如何公正、合理地行使國家刑罰權(quán)力、有效維護(hù)社會(huì)秩序的問題上,常識(shí)化理解必須讓位于專業(yè)化解釋。
常識(shí)化與專業(yè)性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兩者之間的矛盾集中地表現(xiàn)在:具體案件適用法律的過程中,究竟是以專業(yè)化解釋的規(guī)范性、確定性為指導(dǎo),避免常識(shí)觀念的任意性、變化性,還是以常識(shí)觀念為標(biāo)準(zhǔn)衡量專業(yè)化解釋的合理性、有效性。對(duì)于這個(gè)問題,不僅實(shí)務(wù)部門的一些同志存在模糊的認(rèn)識(shí),而且在學(xué)理研究領(lǐng)域也是“見仁見智”。一方面強(qiáng)調(diào)要尊重國民法律情感和規(guī)范性意識(shí),主張“刑法解釋的正確與否取決于一般國民的判斷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根據(jù)“違法性意識(shí)不要說”,行為人對(duì)法律認(rèn)識(shí)的正確與否并不影響法律的適用,強(qiáng)調(diào)法律規(guī)范的內(nèi)容及適用應(yīng)當(dāng)以司法機(jī)關(guān)的專業(yè)性認(rèn)識(shí)為標(biāo)準(zhǔn)來確定[8]。刑法不僅是一般的行為規(guī)范,作為制裁法的裁判規(guī)范,它的遵守和適用直接涉及對(duì)法益保護(hù)的有效性、及時(shí)性,也關(guān)系到規(guī)范司法、保障人權(quán)的公正性、正義性。由于專業(yè)與常識(shí)之間的差別使得法律的遵守和法律的適用在某些場(chǎng)合下不相一致,這種情況會(huì)不同程度地影響刑法功能的發(fā)揮。因此,刑法解釋首先要面對(duì)的就是如何將專業(yè)性的知識(shí)轉(zhuǎn)化為一般公眾的常識(shí)觀念。
常識(shí)化解釋的另一個(gè)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刑法學(xué)的理論問題。理論是任何一門科學(xué)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理論,或者相關(guān)的知識(shí)體系不能被稱之為理論,我們就不能將其視為科學(xué)。人們通常將書本對(duì)法律的理解和解釋,或者學(xué)者們的某些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稱之為“刑法理論”是有道理的,這是由于書本上的內(nèi)容和學(xué)者們的觀點(diǎn)通常不是針對(duì)某一具體案件中的特殊問題直接給出答案,而是從一般性的角度說明這類問題所對(duì)應(yīng)的基本原則和普遍原理,因?yàn)椤叭魏我粋€(gè)具體的事例都是偶然的、特殊的”,而理論只關(guān)心它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國,刑法學(xué)書籍基本上都是從經(jīng)驗(yàn)或者技術(shù)性的層面對(duì)刑法條文進(jìn)行解釋,圍繞具體案件的事實(shí)情節(jié)討論行為所構(gòu)成的個(gè)罪罪名。例如,關(guān)于搶劫罪與敲詐勒索罪是否要求有暴力行為的實(shí)施、是否要求當(dāng)場(chǎng)劫取財(cái)物的爭論;企業(yè)改制后國家工作人員性質(zhì)認(rèn)定中的“委派”應(yīng)當(dāng)如何理解;預(yù)謀綁架,采取先殺人后勒索財(cái)物的行為究竟是認(rèn)定綁架罪還是認(rèn)定故意殺人罪、是一罪還是數(shù)罪等等。還有一些書籍采取的是望文生義的解釋方法,例如,對(duì)刑法中犯罪故意的解釋:在認(rèn)識(shí)方面,必須是明知,所謂“明知”是對(duì)自己行為和結(jié)果可能發(fā)生或者必然發(fā)生有認(rèn)識(shí);在意志方面,必須持有希望或放任的態(tài)度,“希望”就是追求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放任”就是對(duì)結(jié)果的發(fā)生聽之任之。又如,對(duì)“共犯”的解釋:共同犯罪也稱“共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對(duì)“重罪”的解釋:是指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自由刑、死刑的犯罪;對(duì)法條競合的解釋:一個(gè)行為同時(shí)觸犯了兩個(gè)法律條文等等。從這些書籍中我們不但找不到理論性的表述,甚至找不到專業(yè)化的痕跡。坦誠地說,筆者并不認(rèn)為立足于解決司法實(shí)踐中的具體問題而對(duì)刑法條文作出通俗的解釋有什么不當(dāng)之處,然而,單就這種解釋來看的確毫無理論性可言。
理論和實(shí)踐是兩個(gè)不同的概念,我們說:“理論不能脫離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或者“理論來源于實(shí)踐經(jīng)驗(yàn)”這是正確的,但是有一點(diǎn)必須清楚,那就是理論不是實(shí)踐。理論與實(shí)踐是有區(qū)別的,因?yàn)樗皇歉行哉J(rèn)識(shí),不是可以直接操作的技術(shù)、技能,更不是生活經(jīng)驗(yàn),如果不明確兩者之間的界限或者將他們混同起來,至少是一種誤解。應(yīng)當(dāng)看到,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學(xué)研究中十分注重理論的嚴(yán)謹(jǐn)性,盡管那些國家的刑法學(xué)者們也是以自己國家的刑法典為特殊研究對(duì)象,但他們是站在刑法的客觀性、規(guī)律性和目的性立場(chǎng)上闡述法律規(guī)范的社會(huì)意義和普遍價(jià)值的。我們經(jīng)常以法律文化傳統(tǒng)、社會(huì)制度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上的差異為借口拒斥外國刑法理論研究取得的科學(xué)成果,甚至以極為輕蔑的態(tài)度歪曲刑法理論中的基本原理,可是這些我們始終在不斷批判的基本原理,卻時(shí)時(shí)刻刻地涉及我國犯罪構(gòu)成學(xué)說和刑罰論的知識(shí)領(lǐng)域中的每一個(gè)具體問題。例如,我國刑法學(xué)肯定社會(huì)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zhì)特征,但卻不贊同結(jié)果無價(jià)值學(xué)說的有效性;承認(rèn)主觀故意或過失與客觀危害行為的統(tǒng)一是成立犯罪的基本條件,卻否認(rèn)心理責(zé)任的合理性;擁護(hù)在無責(zé)任能力、意外事件和不可抗力的情況下不能成立犯罪,卻拒絕接受期待可能性學(xué)說和規(guī)范責(zé)任的客觀性;堅(jiān)持刑事責(zé)任是法律對(duì)犯罪人的譴責(zé)和否定,卻無視有責(zé)性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條件等等。在與外國刑法學(xué)研究方法的比較中會(huì)發(fā)現(xiàn),我國刑法學(xué)領(lǐng)域缺乏的是在概念思維指導(dǎo)下的理論研究,而理論研究的不斷發(fā)展是刑法科學(xué)走向成熟的重要標(biāo)志。
理論與實(shí)踐之間的差別導(dǎo)致了一個(gè)現(xiàn)實(shí)性的問題:在實(shí)踐中,刑法作為行為規(guī)范是面向全體社會(huì)成員的,所以,對(duì)刑法條文的注釋和對(duì)法律規(guī)范內(nèi)容的說明應(yīng)當(dāng)通俗易懂、貼近日常生活,以方便人們的普遍遵守;另一方面,作為法律科學(xué)的刑法學(xué)是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知識(shí)體系,作為裁判規(guī)范的刑法是針對(duì)法律職業(yè)群體而言的。對(duì)刑法條文的“熟知”與對(duì)法律規(guī)范的“真知”之間是有區(qū)別的,檢察官、律師和法官們對(duì)刑法作出的解釋并不局限于法條文字的常識(shí)性注釋,還要對(duì)刑法適用的目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之間的邏輯關(guān)系等專業(yè)性問題有較為清楚和準(zhǔn)確的認(rèn)識(shí);以刑法規(guī)范為研究對(duì)象的研究者們,還要對(duì)刑法的“概念框架”、“體系結(jié)構(gòu)”、“價(jià)值評(píng)判的標(biāo)準(zhǔn)”、“罪刑關(guān)系的理論根據(jù)”和“刑法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等方面的問題作出分析、評(píng)價(jià)和詮釋。從科學(xué)的角度來看,刑法理論的魅力不在于它對(duì)刑罰法規(guī)的適用范圍和條件作出如何生動(dòng)的經(jīng)驗(yàn)性表述,也不在于從現(xiàn)象層面對(duì)個(gè)案事實(shí)與構(gòu)成要件的符合性演繹多么合情合理,而是集中地表現(xiàn)在它對(duì)刑法概念框架的邏輯建構(gòu)、對(duì)罪刑基本關(guān)系的思辨和對(duì)刑罰價(jià)值判斷標(biāo)準(zhǔn)的反省。質(zhì)言之,在刑法的遵守和適用等實(shí)踐的層面,刑法學(xué)中的法條解釋只能是常識(shí)化、經(jīng)驗(yàn)性的,而在刑法科學(xué)的層面,理論作為條文注釋的科學(xué)根據(jù)、解釋規(guī)則和客觀標(biāo)準(zhǔn),則應(yīng)當(dāng)是抽象、思辨和超驗(yàn)的。
三、常識(shí)化的科學(xué)解釋與效力解釋
刑法教科書根據(jù)解釋主體的不同,將刑法解釋的種類劃分為“立法解釋”、“司法解釋”和“學(xué)理解釋”,這種劃分主要是從實(shí)踐的角度來考慮解釋效力的權(quán)威性。在司法實(shí)踐中,當(dāng)人們對(duì)刑罰法規(guī)的理解和應(yīng)用發(fā)生爭論和分歧時(shí),尤其是分歧發(fā)生在刑法專業(yè)知識(shí)的范圍時(shí),以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為標(biāo)準(zhǔn)理解和適用刑法的規(guī)定,將效力解釋視為對(duì)法律條文的正確答案似乎是一條普遍的真理。同時(shí),檢驗(yàn)各種意見或觀點(diǎn)是否正確,不僅以法律條文的規(guī)定為尺度,而且必須與效力性解釋相一致、相符合。然而,從科學(xué)研究的角度,肯定和支持刑法規(guī)范解釋的效力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還必須以理論的科學(xué)性為根據(jù)對(duì)效力解釋的合理性、客觀性做出分析、評(píng)價(jià)和判斷。因?yàn)樵诳蒲蓄I(lǐng)域中,只有客觀、合理地理解和運(yùn)用刑法規(guī)范,才能真正地實(shí)現(xiàn)刑罰的目的,才具有權(quán)威性。由于刑罰法規(guī)的客觀性、真理性并不自發(fā)地包含在效力性解釋之中,所以解釋的效力性絕不能代替或者等同于“刑罰法規(guī)”自身的科學(xué)性、合理性。當(dāng)然,效力解釋與科學(xué)解釋并不是對(duì)立的,筆者也無意否認(rèn)效力解釋中的科學(xué)性成分,但是科學(xué)性與效力性畢竟是有差別的,刑法解釋的效力性與科學(xué)性之間,既有相互聯(lián)系、統(tǒng)一和諧的一面,也有相互區(qū)別、對(duì)立沖突的一面。刑法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重要課題,就是如何實(shí)現(xiàn)科學(xué)解釋與效力解釋的統(tǒng)一。無需諱言,在司法實(shí)踐中,“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釋未必合理,而科學(xué)的解釋因不具有效力而被否定”的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的,在刑法解釋中,“效力優(yōu)先”原則是一個(gè)不爭的事實(shí)。
常識(shí)性解釋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在于它能夠使得人們對(duì)法律規(guī)定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統(tǒng)一起來,而效力解釋的重要作用恰恰業(yè)也在于此。法律作為社會(huì)行為規(guī)范,能否得到社會(huì)公眾的普遍理解和接受,直接關(guān)系到法律社會(huì)功能的實(shí)現(xiàn),然而,刑法公正與效率的有機(jī)統(tǒng)一不僅在于人們對(duì)法律認(rèn)識(shí)的一致性、無差別性,更在于社會(huì)公眾能否準(zhǔn)確、客觀地認(rèn)識(shí)和遵守刑法規(guī)范提出的各項(xiàng)要求。對(duì)法律的任何理解都是基于認(rèn)知主體的利益和需要而產(chǎn)生的,都會(huì)融入認(rèn)知主體的目的和愿望。刑法解釋的科學(xué)性并不在于排斥這些主觀因素的存在,而是要認(rèn)真探索和努力實(shí)現(xiàn)對(duì)刑法理解的“合規(guī)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tǒng)一”。效力性解釋首先解決了法律認(rèn)識(shí)的統(tǒng)一性問題,而科學(xué)解釋則更加關(guān)注如何引導(dǎo)社會(huì)公眾在正確、客觀的基礎(chǔ)上統(tǒng)一人們對(duì)法律的認(rèn)識(shí),刑法的效力解釋只有建立在法律科學(xué)的基礎(chǔ)之上,才能不但在實(shí)踐中而且在科學(xué)領(lǐng)域具有真正的權(quán)威性。質(zhì)言之,引導(dǎo)人們更加合理、更加科學(xué)地理解、遵守和應(yīng)用刑法規(guī)范,是效力解釋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標(biāo)。刑法的效力解釋通常是建立在常識(shí)或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之上的,作為經(jīng)驗(yàn)和常識(shí)中的法律是一種表象,現(xiàn)象是不斷變化的,除非能夠把握它的本質(zhì)。在經(jīng)驗(yàn)范圍內(nèi)解決對(duì)刑法認(rèn)識(shí)的分歧是難以得出確定答案的,唯一的方法是依賴解釋的效力性。而在科學(xué)范圍內(nèi)衡量法律解釋合理性的方法卻有所不同,既可以通過程序的合法性來保障實(shí)體的合理,也可以通過理論的科學(xué)性檢驗(yàn)解釋的客觀性。科學(xué)解釋與效力解釋之間的矛盾是常識(shí)化解釋必須回答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
在筆者看來,刑法解釋有廣狹二義之分,狹義的刑法解釋是對(duì)法律條文的注釋和說明,主要是解決具體事實(shí)與構(gòu)成要件的符合性問題;廣義的刑法解釋除了對(duì)刑法條文的注解之外,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對(duì)刑法的邏輯結(jié)構(gòu)、概念框架、本質(zhì)特征、基本原則、客觀規(guī)律、價(jià)值理念、思維方式等方面內(nèi)容的建構(gòu)、辨析、整合、詮釋和探索。任何科學(xué)都是關(guān)于其研究對(duì)象的分析和解釋,離開了對(duì)研究對(duì)象的科學(xué)分析和解釋,也就不存在所謂的科學(xué)領(lǐng)域。換言之,所謂刑法科學(xué),實(shí)際上就是對(duì)刑法規(guī)范整體作出的解釋和說明,從這一意義上說,刑法學(xué)實(shí)際上就是“刑法解釋學(xué)”。刑法科學(xué)不但要對(duì)具體應(yīng)用法律條文的問題作出合理解釋,更要對(duì)刑法規(guī)范在適用中的規(guī)律性問題與目的性問題作出確定的說明。針對(duì)不同的需要采用不同的解釋方法,而各種不同的解釋方法又統(tǒng)一于刑法科學(xué)的客觀性和目的性之中。
在法律遵守和法律適用中,對(duì)法條文字的原本含義作出(典型性)的說明,按照法條文字、詞語的一般意義對(duì)刑法規(guī)范的內(nèi)容和適用范圍進(jìn)行經(jīng)驗(yàn)的、通俗的解釋,無疑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然而,一旦進(jìn)入更為廣闊的領(lǐng)域,這種方法的局限性就會(huì)明顯地暴露出來。
正如恩格斯在評(píng)價(jià)形而上學(xué)思維方式的時(shí)候曾經(jīng)指出的那樣:常識(shí)在日常活動(dòng)范圍內(nèi)雖然是極可尊敬的東西,但是一跨入廣闊的研究領(lǐng)域,就會(huì)遇到驚人的變故。……一旦超過這個(gè)界限,它就會(huì)變成片面的、狹隘的,并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9]由于立法技術(shù)、社會(huì)發(fā)展以及立法者認(rèn)知能力等方面的原因,刑法規(guī)范的模糊性、不確定性、疏漏、空缺和滯后性等問題會(huì)在司法實(shí)踐中不斷地出現(xiàn),給刑法的適用和遵守帶來一定影響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結(jié)合特定的背景環(huán)境和具體的行為事實(shí),對(duì)法律規(guī)定作出相關(guān)的解釋和說明時(shí),如果完全從文字的一般含義、條文詞語的日常理解來解釋法律規(guī)范的要求和應(yīng)用,就會(huì)陷入各種疑惑和困擾。也就是說,由于法律規(guī)定無法避免的缺陷以及社會(huì)發(fā)展的需要,刑法規(guī)范在其具體應(yīng)用的過程中,法律解釋也會(huì)不斷地發(fā)生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會(huì)超出刑法的目的和功能的范圍,更不能改變刑法的本質(zhì)和發(fā)展規(guī)律。質(zhì)言之,解釋的變化必須在科學(xué)理論的指導(dǎo)下才具有確定性、客觀性。倘若從常識(shí)知識(shí)或者感性經(jīng)驗(yàn)的角度出發(fā),解釋的變化性就可能導(dǎo)致對(duì)法律條文理解的任意性和解釋的隨意性,因?yàn)槊撾x了科學(xué)理論的客觀標(biāo)準(zhǔn),就無法檢驗(yàn)我們認(rèn)識(shí)的合理性、正確性。在專制制度下,權(quán)力者的主張就是最正確、最合理、最具有權(quán)威性的,而在民主制度下,法律的終極目標(biāo)、客觀規(guī)律和價(jià)值觀念決定著裁判者應(yīng)當(dāng)如何作出選擇。
刑法,是對(duì)司法機(jī)關(guān)和法官追究、裁判犯罪人責(zé)任等司法活動(dòng)的規(guī)制和限定,代表國家行使刑罰權(quán)的司法機(jī)關(guān)和裁判者,必須認(rèn)真履行職責(zé),必須根據(jù)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專業(yè)性技術(shù)要求解釋法律、適用刑法。無論從法律專業(yè)知識(shí)的掌握,還是司法、審判經(jīng)驗(yàn)的積累,或者是對(duì)刑法的整體性了解以及對(duì)刑事政策基本精神的領(lǐng)會(huì),以法官為代表的法律職業(yè)群體對(duì)法律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與社會(huì)一般公民的法律意識(shí)之間是有很大差別的,這種差別不但要反映在專業(yè)知識(shí)的系統(tǒng)性與技術(shù)規(guī)范的確定性方面,更重要的是要表現(xiàn)在對(duì)科學(xué)理論的認(rèn)知與反省。引導(dǎo)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shí)和法制觀念,這是法律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解釋的一項(xiàng)重要任務(wù)。
人們對(duì)法律的認(rèn)識(shí)通常取決于他們對(duì)法律的需要,希望法律給他們帶來安全、保護(hù)他們的權(quán)益。所以,人們對(duì)法律的理解是根據(jù)自身的需要和在不同層次上進(jìn)行的。從整體上看,對(duì)法律的需要大致可以包括三個(gè)層次:(1)在行為規(guī)范的范圍內(nèi),一般公民從守法和保護(hù)自己合法權(quán)益的立場(chǎng)上形成的對(duì)法律認(rèn)識(shí)和理解的需要,所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保護(hù);(2)在裁判規(guī)范的適用中,作為法律職業(yè)群體的實(shí)務(wù)工作者,根據(jù)各自的訴訟地位從法律應(yīng)用的角度產(chǎn)生的對(duì)法律規(guī)范解釋和說明的需要,期盼的是解決“定罪量刑”的合理性、均衡性問題;(3)在科學(xué)研究的領(lǐng)域內(nèi),理論工作者從法學(xué)基本原理的視角所萌發(fā)的對(duì)刑法規(guī)范詮釋和構(gòu)筑的需要,探尋的是刑法合目的性與合規(guī)律性統(tǒng)一的途徑和實(shí)質(zhì)。正是由于對(duì)刑法規(guī)定理解的各種不同需要,決定了刑法解釋層次劃分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三種需要是相互聯(lián)系的,但它們之間的差別性是顯而易見的,要實(shí)現(xiàn)在對(duì)法律規(guī)范理解、遵守和應(yīng)用上的一致性,應(yīng)當(dāng)有一個(gè)統(tǒng)一的基礎(chǔ)和相互融合的條件。片面地強(qiáng)調(diào)效力解釋的權(quán)威性是不妥當(dāng)?shù)模M管這是一種客觀現(xiàn)實(shí)。在筆者看來,真正滿足社會(huì)整體需要的基礎(chǔ)和條件應(yīng)當(dāng)是效力性與科學(xué)性的有機(jī)統(tǒng)一。效力性是暫時(shí)的、有條件的、相對(duì)的,而以客觀性與目的性結(jié)合為主要內(nèi)容的科學(xué)性則是永恒的、無條件的、絕對(duì)的。
四、常識(shí)化解釋的合理性認(rèn)知
刑法的常識(shí)化解釋在司法實(shí)踐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這一點(diǎn)是有目共睹、無可置疑的,但是在刑法知識(shí)的常識(shí)化普及過程中,我們還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無論在法律實(shí)踐的范圍還是在學(xué)理研究的領(lǐng)域,普遍存在著一種誤解,這種理解上的偏誤概括起來有兩個(gè)方面:一是刑法解釋中存在的“專業(yè)知識(shí)常識(shí)化的傾向”,即將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與刑法專業(yè)知識(shí)等同起來不加區(qū)分,把符合常識(shí)觀念視為刑法解釋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和途徑,以社會(huì)公眾的法律情感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為基準(zhǔn),統(tǒng)一人們對(duì)刑法規(guī)范的理解和認(rèn)識(shí),以行為規(guī)范的標(biāo)準(zhǔn)指導(dǎo)裁判規(guī)范的應(yīng)用;二是混淆刑法學(xué)中職業(yè)技術(shù)知識(shí)和法律科學(xué)之間的界限,將感性經(jīng)驗(yàn)等同于科學(xué)理論,堅(jiān)信“理論”的唯一價(jià)值就是直接對(duì)應(yīng)個(gè)別現(xiàn)象,解決具體問題。刑法理論應(yīng)當(dāng)與生活實(shí)踐一樣,具有直觀性、可感性和可操作性。
(一)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的專業(yè)化反省
刑法的專業(yè)知識(shí)與“人情常理”都具有可感性、直觀性的特點(diǎn),在對(duì)具體現(xiàn)象進(jìn)行分析和描述時(shí),兩者相互結(jié)合、相互滲透密切聯(lián)系的情況是經(jīng)常發(fā)生的。例如,常識(shí)觀念中的故意和過失與刑法主觀要件的含義十分接近,甚至在典型案例中幾乎沒有什么差別,所以在理解上并不會(huì)出現(xiàn)什么障礙。然而,當(dāng)出現(xiàn)復(fù)雜情節(jié)的時(shí)候,故意、過失作為構(gòu)成要件與日常生活用語兩者的區(qū)別就明顯地暴露出來,這種現(xiàn)象在司法實(shí)踐中屢見不鮮。例如,在防衛(wèi)過當(dāng)中,防衛(wèi)人存在著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故意要素,同時(shí)又存在著防衛(wèi)不法侵害的故意。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故意作為犯罪成立的條件,防衛(wèi)不法侵害的故意,則作為阻卻或減免責(zé)任的要素,如果不具備后者則不能認(rèn)定為防衛(wèi)過當(dāng)。在這種情況下,不但存在與日常生活中故意的不同,還存在著構(gòu)成要件故意與責(zé)任故意的區(qū)別。由于我們將常識(shí)中的詞匯與專業(yè)術(shù)語相混淆,那么,由于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的不確定性、多義性,必然會(huì)導(dǎo)致法律解釋出現(xiàn)分歧和爭論。這些問題不但困擾著司法實(shí)務(wù)部門,而且經(jīng)常成為教學(xué)科研領(lǐng)域的主要話題。因此,無論專業(yè)知識(shí)與常識(shí)性認(rèn)識(shí)在某些方面如何接近,兩者的界限必須明確。在教科書和司法解釋中,或許是為了方便人們對(duì)刑法規(guī)范的理解和接受,并沒有對(duì)兩者作出嚴(yán)格地區(qū)分,這就很容易造成一種錯(cuò)覺:原來所謂的專業(yè)人員、學(xué)者也是在常識(shí)層面上理解法律規(guī)范內(nèi)容的呀!那他們對(duì)法律的理解與社會(huì)一般公眾是不應(yīng)當(dāng)有什么區(qū)別的啊!所不同的就是由于職務(wù)或職業(yè)的特殊性,使他們對(duì)法律條文更熟悉一些,接觸的案件更多一點(diǎn)、相關(guān)的司法解釋了解得更多一些、更早一些而已。這樣一來,就會(huì)經(jīng)常出現(xiàn)沒有學(xué)過法律的人,從常識(shí)的立場(chǎng)反對(duì)和批評(píng)熟悉專業(yè)知識(shí)的司法人員和“資深的學(xué)者”對(duì)法律問題作出的判斷和觀點(diǎn)(當(dāng)然他們是有權(quán)利這樣做的),盡管這些批評(píng)和反對(duì)意見有許多是錯(cuò)誤的、可笑的;法律專業(yè)人員、學(xué)者有時(shí)也會(huì)脫離專業(yè)知識(shí)的基本規(guī)范,根據(jù)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不斷地變換自己的觀點(diǎn),在不同的場(chǎng)合下對(duì)法律規(guī)范作出各種各樣甚至相互矛盾的解釋。
筆者認(rèn)為,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一個(gè)重要原因就是混淆了刑法雙重規(guī)范之間的界限與差別。
刑法首先是作為行為規(guī)范而發(fā)揮作用的,是對(duì)社會(huì)公眾行為提出的要求和限制。刑法與其他法律規(guī)范不同的一個(gè)主要特點(diǎn),就是它對(duì)國民行為的限制和要求不是直截了當(dāng)?shù)模请[含在刑法條文的規(guī)定之中,即只要刑法規(guī)定以刑罰方式加以處罰的行為,就是禁止人們實(shí)施的行為,要求國民以刑罰法規(guī)的存在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不得實(shí)施法律以刑罰方式所禁止的行為”。例如,刑法規(guī)定: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jié)較輕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表面上看,條文只規(guī)定了刑罰適用的條件和范圍,但是其中包含了“不得殺人”這一行為規(guī)范的前提。
從行為規(guī)范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刑法必須符合社會(huì)公眾的法律情感和國民的法律意識(shí),這對(duì)于公民接受、遵守法律和預(yù)防犯罪是極為重要的。日本學(xué)者曾根威彥認(rèn)為:作為行為規(guī)范,刑法基本上與社會(huì)倫理規(guī)范相一致,所以不在刑法規(guī)定中明文顯示,而只規(guī)定有關(guān)裁判規(guī)范的內(nèi)容。行為人在意圖作出某種行為的選擇時(shí),必須能夠判斷自己的行為是不是為刑法所允許,只要不實(shí)施法律禁止的行為,就絕對(duì)不應(yīng)當(dāng)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刑法保證國民行動(dòng)自由的重要方面。作為行為規(guī)范;從一般人的立場(chǎng)以及根據(jù)行為時(shí)的事實(shí)理解和解釋刑法規(guī)定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然而,刑法更重要的是作為裁判規(guī)范約束和規(guī)制法官審判行為,從裁判規(guī)范的立場(chǎng)出發(fā),刑法具有命令法官按照法律規(guī)定進(jìn)行裁判的作用。作為規(guī)制社會(huì)手段的刑法,最為重要的意義在于,通過約束實(shí)際適用刑法的法官的判斷和行動(dòng),防止根據(jù)國家刑罰權(quán)任意地適用刑罰,而單純強(qiáng)調(diào)刑法行為規(guī)范的特點(diǎn)就會(huì)忽視刑法的這種存在的意義,這是值得提防的。[10] 從行為規(guī)范的立場(chǎng),任何背離國民意識(shí)、公眾觀念的法律解釋都將被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官或者其他法律職業(yè)群體要放棄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術(shù)規(guī)范,無條件地服從公民對(duì)法律的常識(shí)化認(rèn)識(shí)。作為法律解釋的一種方法,常識(shí)化主要是從法律遵守和刑法應(yīng)用的實(shí)踐出發(fā)的,將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術(shù)性問題轉(zhuǎn)換為公眾語言或常識(shí)觀念,是為了使人們能夠普遍地接受和認(rèn)同刑罰法規(guī),引導(dǎo)公民更加科學(xué)、合理地理解法律提出的要求,自覺地遵守法律規(guī)范,實(shí)現(xiàn)法律對(duì)社會(huì)公眾行為的規(guī)制的有效性。只有在這個(gè)前提下,常識(shí)化解釋才是正確的、有意義的,而不是為了將人們對(duì)法律的理解限制在常識(shí)化的認(rèn)識(shí)水平,或者片面地追求專業(yè)知識(shí)常識(shí)化,將法官的法律素養(yǎng)等同于一般老百姓的常識(shí)觀念。
(二)感性經(jīng)驗(yàn)的理論批判
刑法專業(yè)知識(shí)在許多方面并不屬于理論的范疇,確切的說在這些知識(shí)中絕大部分屬于未加概括和歸納的感性經(jīng)驗(yàn),盡管這些感性認(rèn)識(shí)在處理具體問題時(shí)可能會(huì)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但我們還是不能夠?qū)⑦@些內(nèi)容稱其為理論。
當(dāng)代法學(xué)研究成果認(rèn)為,法學(xué)和法律科學(xué)不是同一邏輯層面上的概念,法學(xué)既包括法律科學(xué)又包括關(guān)于法律的學(xué)問。而法律科學(xué)與關(guān)于法律知識(shí)的學(xué)問,起碼有兩個(gè)方面的不同:[11]
其一,從方法上看,法律科學(xué)是運(yùn)用科學(xué)的方法對(duì)法律現(xiàn)象進(jìn)行系統(tǒng)而深入的研究,對(duì)法律知識(shí)進(jìn)行準(zhǔn)確(盡量科學(xué)化)地表述,而關(guān)于法律的學(xué)問則不一定要用科學(xué)的方法進(jìn)行概括和總結(jié)。比如古代社會(huì)關(guān)于法律的一些知識(shí)我們很難稱之為科學(xué),但我們誰也不否認(rèn)古人關(guān)于法律的知識(shí)具有一定程度的學(xué)問。其二,從研究的結(jié)果上看,法律科學(xué)得出的結(jié)論應(yīng)當(dāng)是規(guī)律性的東西,因?yàn)榭茖W(xué)的任務(wù)之一就是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zhì),揭示事物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但是我們看到的大量關(guān)于法律研究的成果,幾乎都是仁智之見,究竟哪些成果屬于科學(xué)的范疇實(shí)在難以定論。甚至有學(xué)者認(rèn)為,誰也不能否認(rèn)法律科學(xué)的存在,但誰的研究成果是科學(xué)的,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gè)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因而多數(shù)法學(xué)著作都可被視為關(guān)于法律的知識(shí)和學(xué)問。
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學(xué)者通常將刑法學(xué)作為一門法律科學(xué)來研究,尤其是德國和日本的刑法學(xué)者,他們對(duì)刑法學(xué)體系的構(gòu)造、基本概念的邏輯關(guān)系所作出的闡述和理論思維的方法,完全是從科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的;而英美法系的一些國家,則更多是將法學(xué)視為一種職業(yè)技術(shù)。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很多人將法學(xué)院的法學(xué)課程視為一種高級(jí)的職業(yè)技術(shù)訓(xùn)練,也有一部分學(xué)者把法學(xué)視為關(guān)于法律的知識(shí)和經(jīng)驗(yàn)的學(xué)問。[12]我國有學(xué)者指出,英美法理論的邏輯起點(diǎn)是經(jīng)驗(yàn),價(jià)值目標(biāo)是實(shí)用;大陸法系理論思維的邏輯起點(diǎn)是概念,價(jià)值目標(biāo)是完善。[13]由此可見,刑法學(xué)本身存在著專業(yè)經(jīng)驗(yàn)和科學(xué)理論兩個(gè)不同的層面,它們?cè)谛谭▽W(xué)中有其各自的地位和特殊的功能。從法律遵守和應(yīng)用的角度,刑法學(xué)側(cè)重于實(shí)用性、操作性、具體性和經(jīng)驗(yàn)性,是一種以經(jīng)驗(yàn)為基礎(chǔ)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職業(yè)技能;從法律科學(xué)的立場(chǎng),刑法學(xué)研究的問題則是刑法的客觀性、合理性、目的性和普遍性,是一種建立在基本概念和邏輯思維基礎(chǔ)上的理論體系。由于兩者在刑法學(xué)研究中是不可分離的,因此,從當(dāng)代刑法學(xué)研究的發(fā)展趨向上看,大陸法系國家以較為成熟的刑法理論為基礎(chǔ),更加關(guān)注實(shí)踐操作中具體問題的討論,而英美法系國家則以普通法為根基,愈加注重刑法理論層面的研究。[14]刑法學(xué)作為法學(xué)的一個(gè)重要的學(xué)科,既是一門科學(xué)理論又是一種職業(yè)技能,所以,對(duì)刑法的解釋既有常識(shí)化、經(jīng)驗(yàn)性和可操作性的一面,同時(shí)又具有科學(xué)性、概念性和客觀性的一面,兩個(gè)方面既是緊密結(jié)合、相互聯(lián)系的,又有嚴(yán)格的界限和不同的功能。
刑法學(xué)作為職業(yè)技術(shù)、專業(yè)技能方面的知識(shí),在常識(shí)觀念的領(lǐng)域內(nèi)是極受歡迎和尊敬的。在這一范圍內(nèi),刑法條文、司法解釋與常識(shí)知識(shí)是一致的、無差別的,任何具有一定文化知識(shí)和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的人都能夠理解法律或司法提出的要求和限制。“不因不知法而免責(zé)”的法諺甚至要求文化水平更低的人也必須知曉法律的內(nèi)容不得違反規(guī)范。在大多數(shù)刑法條文中,法律規(guī)定是用通俗化的語言表述的,諸如“故意殺人”、“竊取財(cái)物”、“放火”、“偽造貨幣”等等,這些在立法時(shí)已經(jīng)考慮到社會(huì)公眾接受和理解的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無需進(jìn)行解釋。有一些規(guī)定雖然條文表述使用了行業(yè)術(shù)語,涉及某些專業(yè)或技術(shù)等方面的知識(shí),由于是對(duì)某一特定領(lǐng)域中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規(guī)定,所以,盡管一般社會(huì)公眾可能在理解上會(huì)有一些困難,但行為人通常是具有相關(guān)專業(yè)知識(shí)和認(rèn)識(shí)能力的人員,對(duì)于他們來說也無需做出特別的解釋。例如,經(jīng)濟(jì)犯罪中關(guān)于違反公司法、金融法規(guī);違反商標(biāo)法、專利法;違反稅法、工商管理法規(guī)等規(guī)定,對(duì)這些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解釋仍然是現(xiàn)象的、經(jīng)驗(yàn)性的,并不具有理論的普遍性。[15]
作為操作規(guī)則和專業(yè)技能方面知識(shí)的刑法學(xué),具有實(shí)用性、直觀性和可操作性,會(huì)為我們提供一些重要的經(jīng)驗(yàn)、方法和技巧,例如,具體案件適用法律的問題上,經(jīng)驗(yàn)可以幫助我們通過個(gè)別事實(shí)的對(duì)照比較,提供曾經(jīng)被使用過的各種選擇方案,推測(cè)該案最終的判決結(jié)果;或者可以通過法院以往判決的經(jīng)驗(yàn)性分析,衡量當(dāng)前案件事實(shí)是否可以適用該法條的規(guī)定,甚至將過去的“判決理由”作為該案定罪量刑的依據(jù);其次,經(jīng)驗(yàn)可以告訴我們要密切關(guān)注司法解釋的新動(dòng)向、新內(nèi)容,有哪些“司法解釋”可以為我們?cè)诜治鰝€(gè)案與法律條文時(shí)提供幫助。經(jīng)驗(yàn)會(huì)告訴我們,司法解釋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權(quán)威性;經(jīng)驗(yàn)還可以告訴我們,在什么時(shí)候、在何種立場(chǎng)上如何變換對(duì)法律條文的解釋更有利于自己目的和需要的實(shí)現(xiàn)等等。但是,經(jīng)驗(yàn)總是具體的、特殊的,經(jīng)驗(yàn)會(huì)使概念表象化,混淆現(xiàn)象與本質(zhì)的區(qū)別。
刑法學(xué)作為一門法律科學(xué)是對(duì)刑法規(guī)范和刑法思想的詮釋與建構(gòu),它不但要分析和說明刑法條文中含蘊(yùn)著的規(guī)范內(nèi)容,還要闡述和論證刑法的本質(zhì)特征、運(yùn)作規(guī)律和可罰性根據(jù)。刑法學(xué)關(guān)于刑法所有問題的研究都是圍繞著對(duì)刑法的解釋展開的,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刑法學(xué)是關(guān)于刑法解釋的科學(xué),是一門以刑法規(guī)范為解釋對(duì)象的法律學(xué)科。刑法科學(xué)的要求是:關(guān)于刑法條文的解釋應(yīng)當(dāng)是實(shí)證的、經(jīng)驗(yàn)性的,作為條文注釋根據(jù)的刑法理論則應(yīng)當(dāng)具有思辨性、先驗(yàn)性的特點(diǎn)。在科學(xué)的領(lǐng)域內(nèi),常識(shí)化解釋的客觀性、普遍性是受到懷疑的,多變、不真實(shí)的經(jīng)驗(yàn)表象是不能被當(dāng)成真理而成為科學(xué)中的一部分。在這個(gè)領(lǐng)域內(nèi),科學(xué)解釋的權(quán)威性高于效力解釋,對(duì)概念普遍性的理解精確于對(duì)經(jīng)驗(yàn)特殊性的直觀,刑法規(guī)范和法律事實(shí)的客觀性優(yōu)先于“專家學(xué)者”們經(jīng)驗(yàn)認(rèn)識(shí)的主觀性。混淆經(jīng)驗(yàn)性認(rèn)識(shí)和刑法理論的界限,并將此誤認(rèn)為是“理論與實(shí)踐的有機(jī)結(jié)合”是十分有害的。
【注釋】
[1]陳興良主編:《法治的界面——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刑事法論壇》,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5頁以下。
[2]前引[1],第426.428、434、435頁。
[3](日)大谷實(shí):《刑法總論》,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0、82頁。
[4]前引[3],第162頁。
[5]前引[3],第69—70頁。
[6]在司法實(shí)踐中,社會(huì)公眾確信自己對(duì)法律條文的理解是正確的,對(duì)法官、學(xué)者所作出的解釋不以為然,甚至認(rèn)為是錯(cuò)誤的、不合理的。這種現(xiàn)象說明,常識(shí)觀念是人們認(rèn)識(shí)統(tǒng)一性的基礎(chǔ),在經(jīng)驗(yàn)范圍內(nèi),法官、學(xué)者的解釋如果不能被常識(shí)觀念所接受,其正確性就會(huì)被否認(rèn)。
[7]孫正聿:《哲學(xué)通論》,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41頁以下。
[8]關(guān)于法律認(rèn)識(shí)錯(cuò)誤的問題,究竟以誰的認(rèn)識(shí)為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對(duì)法律認(rèn)識(shí)的正確與否呢?教科書認(rèn)為“行為人對(duì)法律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通常不影響法律適用”的主張,而行為人作為社會(huì)成員,對(duì)法律的認(rèn)識(shí)能力和水平大多表現(xiàn)為常識(shí)化的認(rèn)識(shí)。如果這種認(rèn)識(shí)錯(cuò)誤并不是發(fā)生在個(gè)別人身上,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不是也可以稱為法律的認(rèn)識(shí)錯(cuò)誤呢?
[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1頁。
[10](日)曾根威彥:《刑法學(xué)基礎(chǔ)》,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2頁。
[11]陳金釗:《法律解釋的哲理》,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12]前引[11]。
[13]儲(chǔ)懷植:《美國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
[14](日)曾根威彥:《刑法學(xué)基礎(chǔ)》,黎宏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美)保羅·H.羅賓遜:《刑法的結(jié)構(gòu)與功能》,何秉松等譯,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第1頁(作者序)。